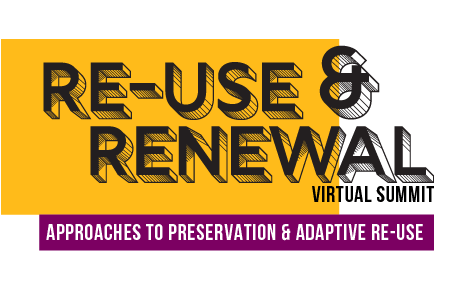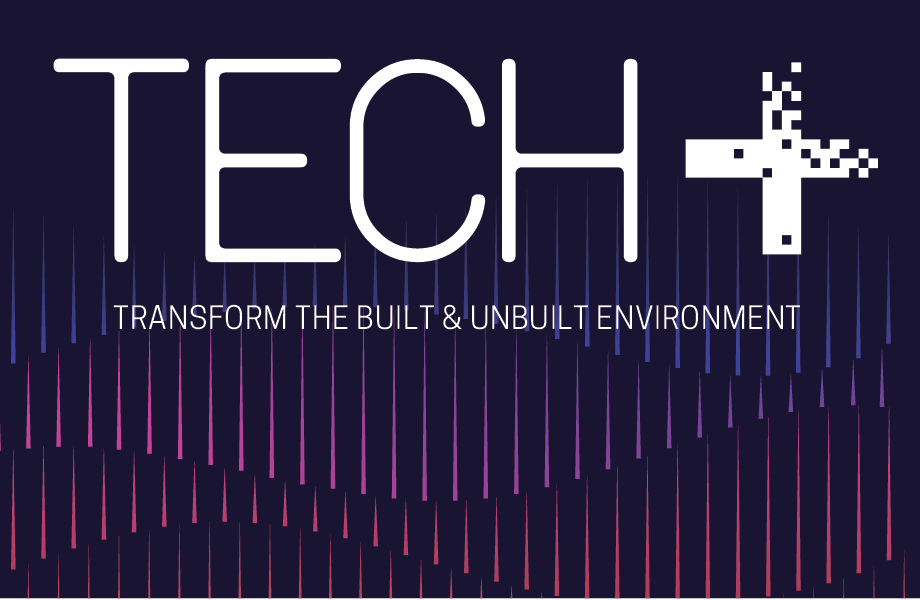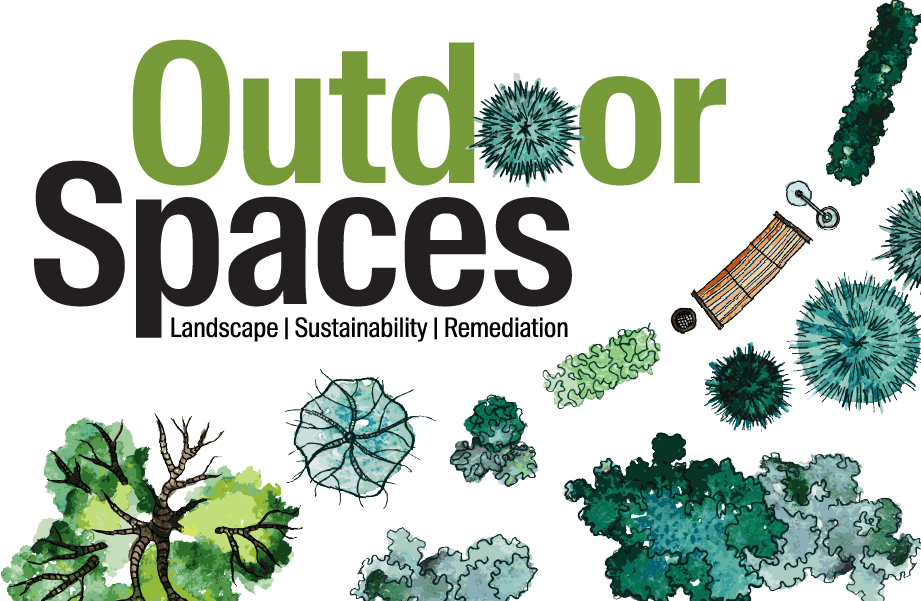建筑师报(AN)与urbanNext-一个多学科的设计平台Actar出版商-每两周分享一次关于共同话题的文章。
这周,我们配对urbanNext文章如下一个的”在这个GSAPP展览中,探索三个近未来的世界,科技改变了浪漫(和城市)本文由Alexis Kalagas、Alfredo Brillembourg和Hubert Klumpner共同撰写。
今天,激进的建筑师或设计师意味着什么?城市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前所未有。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场全面的“全球城市化危机”,具有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态层面[1].从根本上说,城市是充满机遇的地方——毕竟,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移民继续被安全的承诺和向上流动所吸引。但城市往往是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地方,土地、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被转化为排他性增长的症状。面对当代城市化模式,我们不得不质疑城市和城市建设在传统上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我们被迫重新思考如何在城市中运作,从其新兴的智能中学习,并将其结果塑造为激进和战术目的。
激进城市主义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政治领域。想象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包括对现行城市逻辑所产生的空间和社会条件的含蓄批判。因此,我们不仅被提醒勒·柯布西耶他的著名最后通牒“要么建筑,要么革命”,但巴克敏斯特·富勒更具灾难性的宣言“乌托邦,要么被遗忘”与之呼应。[2].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匮乏和紧张,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不断升级的冲突和生态焦虑,这两种情况都是由明显的社会脱节所产生的零和情景。虽然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实验性“后乌托邦”实践浪潮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于对现代运动失败的反对,但这些不同的群体与他们的前辈有着共同的信念——尽管不抱幻想——即根本的差异是可能的,同时也坚信有必要进行突破[3].
(孟买©深港双年展组委会)
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和批判性的有力结合,我们希望在“激进的城市主义”的标题下进行探索——在与社会现实的坚定接触中调和的乌托邦梦想。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在常规的外衣下倡导特殊的人。那些渗透到外围学科,将自己嵌入外部观察者,并利用一个接近的有利位置来影响决策和政策的人。那些放弃直接控制而支持分布式自治和工具性反馈的人。我们对寻求远离学科界限、法律、政治和社会规范的项目感兴趣。这使得同谋成为迫切可能和极不可能,绝对必要和禁忌。一个激进的项目不一定把设计视为解决方案,也不一定把设计视为阐明问题的手段,而是从根本上重组我们生活方式的假设,以及支持这种生活所必需的环境
建筑和城市主义的历史上充斥着个人、团体、运动、结构、未建成的作品、概念项目、研究计划、理论、展览、出版物和表演,这些都是激进意图的强大传统。将这些不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完全逃避学科界限的愿望,而是重新定义建筑和设计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引入替代现状的手段。尽管激进的城市主义可以有无数种形式,但人们可以指出三个潜在的争论领域,它们体现了实践、思想或参与的替代模式。第一种方式是提出一种挑衅的观点,挑战当时的规范思维。第二种是通过重新塑造建筑师的角色,以质疑在干预城市环境时的实际可能性。第三是走在政治变革的前沿,换句话说,建筑就是革命。
如果一个人接受现代主义的基本信念,即解决当代生活的现实意味着在(或通过)城市工作,那么建筑和城市主义可以代表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超越形式和美学的物质问题[5].从尚未实现的愿景和计划,如安东尼奥·圣埃利亚的La Città Nuova,约娜·弗里德曼的Ville Spatiale,康斯坦斯·纽文赫斯的新巴比伦,塞德里克·普莱斯的陶艺思考带,到阿基格拉姆的插电城市,Superstudio的连续的纪念碑,阿奇佐姆的不间断城市,史密森的包容人文主义,潘乔·格德斯的万物有灵论,新陈代谢家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以及像蚂蚁农场,乌托邦和豪斯-拉克-科这样的团体的政治煽动支持,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转变,从对建筑作为离散结构设计的有限理解,到一种扩展的概念,即建筑和城市主义可以体现一种文化批判的形式,或者更果断地冒险进入社会和政治行动领域。
2011年,秘鲁利马附近的实验性proyeecto experimental de Vivienda (PREVI)项目中的一个庭院和一个居民改造房屋。(©深港双年展组委会)
这与一个平行的思路相吻合,即认为建筑师的角色超越了“纯粹的”设计,支持个人和社区的机构,他们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不断变化的建筑环境。我们可以从John Habraken灵活的开放式建筑概念,Walter Segal的简单模块化住房系统,John Turner的自我建造和自我管理理论,Colin Ward的合作策略和“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Riccardo Dalisi与那不勒斯Traiano Quartiere的孩子们的贫困技术,以及Otto Koenigsberger在印度的“行动计划”中看到这一点。除了对最常被权威和控制的正式过程边缘化或排斥的群体或“用户”的共同关注外,这些项目还与一种与现代运动的英雄主义预测形成鲜明对比的谦虚相联系。这是一种激进的城市主义,其特征是对规模和时间的敏感,对背景的欣赏,以及从作者到推动者的转变。
第三种激进是由内而外的,城市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的建筑,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尽管在其最决定论的伪装下——傲慢地相信有能力“在绘图板上纠正社会”——受到质疑。[6]建筑师和设计师与革命性治理的直接结合可能是城市主义最“激进”的表现。虽然这个象征性的案例仍然是Mozei Ginsburg和俄罗斯建构主义者的“社会凝聚器”,它们被有意识地设计来诱导集体主义,但它在Álvaro Siza参与Serviço de Apoio Ambulatório地方(SAAL)住房计划的“旅”中得到了呼应,在葡萄牙革命之后,在1960年代中期军事独裁统治之间的短暂插曲中,在秘鲁启动了proyeecto Experimental de Vivienda (PREVI),以及由BV Doshi的Vāstu-Shilpā顾问公司在独立后的印度设计的周边新城。这些计划配合解放的政治议程,设法巩固其他形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把对更美好世界的梦想描述为20岁真正的“机器里的幽灵”th而塔尔·卡米纳(Tahl Kaminer)则认为,“乌托邦视界”的丧失意味着进步的理念已被视为神话而遭到拒绝[7].那么说当代激进的城市主义有意义吗?简而言之,我们确信它确实如此。城市是复杂的混合空间,不同的行为、思考和生活方式在这里碰撞和转变。在这些空间里,新一代的建筑师、设计师、倡导者、艺术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活动家正在集体重新构想解决关键的城市和社会问题的新策略。今天的这座城市也许比那些在其中运作的人更加激进。它计算未知的可能性,进行高风险的实验,并比负责其管理、分析或设计的大量专业人员更快、更完整地传递先前不可知的未来。
有必要围绕具体和可扩展的项目进行讨论,以重新定义“激进”一词及其在21世纪设计中的潜力圣世纪。的“激进城市主义”展览本次双年展将为追求社会和环境正义、多样性和平等的住房、流动性、生产和娱乐的替代模式带来更多的关注。它将强调激进的实践形式,质疑建筑师的角色,重新定义学科,为建筑和设计思维提出新的领域,新的功能和新的合法性。它将为那些既勇敢又具有挑衅性的项目提供空间,这些项目将引起人们对未来改变游戏规则的城市代理人的关注。它将展示如何在现有权力结构的盲点内合法运作的同时,制定干预和接触的开创性策略。它将重申建筑师和设计师的能力,阐明授权,变革,对抗和可实现的我们共同的城市未来的愿景。
(节选重温城市:2015深港双年展目录, 2016)
本文最初发表于激进城市主义的演变在urbanNext。
[1]大卫·哈维,《全球城市化危机》,载于佩德罗·加达尼奥(编),《不均衡增长:超大城市扩张的战术城市化》(2014)29。
[2]参见勒·柯布西耶,《朝向建筑》(1927);R巴克敏斯特·富勒,《看不见的未来》(1967年12月)11旧金山甲骨文
[3]Fredric Jameson,未来考古学(2005)168。
[4]本文及其他部分摘自深港双年展策展顾问Ersela Kripa和Stephen Mueller撰写的策展声明机构.
[5]约翰·R·戈尔德,《现代主义的经验:现代建筑师与未来城市,1928-53》(2013)15-16。
[6]Meyer Schapiro,“建筑师的乌托邦:建筑与现代生活评论”(1938)4 Partisan Review 44,89 -92。
[7]Reyner Banham,第一次机器时代的理论与设计(2)ndEd, 1980) 12;19. Tahl Kaminer,《建筑、危机与复苏:后福特主义在20世纪晚期建筑中的再现》(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