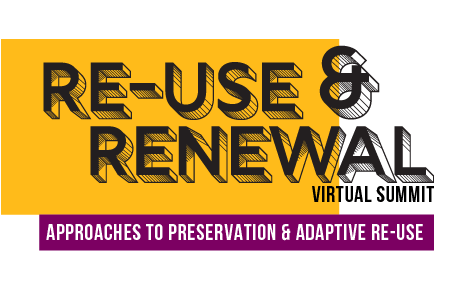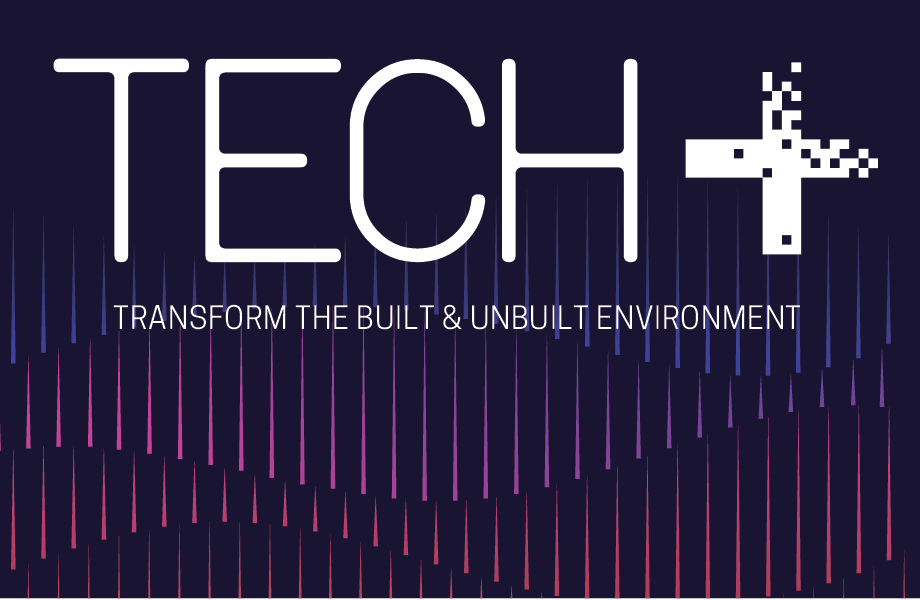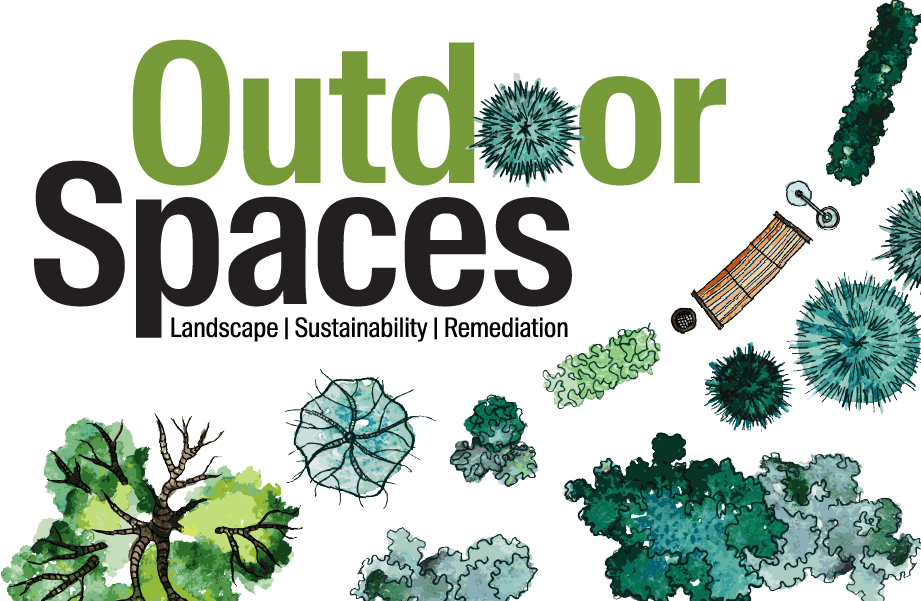尽管我和他一样对当代建筑教育的现状感到担忧,但我的朋友兼同事Peter Zellner在本文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发表的评论让我大吃一惊。
在“建筑教育崩溃了——这里是如何修复它的方法,彼得对当代教育提出了五点批评,并为“后工作室和后数字建筑教育”提出了相应的五点建议。
这些批评来自于25岁的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对这位艺术家近50年前在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开发“后工作室”课程的评论,其目标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师徒关系的等级关系,通常由这种关系导致的学术风格的扩散,以及这种情况经常导致的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沿着一条熟悉但模糊的轨迹展开的,即重视共享知识、自由实验以及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
彼得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尽管有些言过其实。“各种形式的学术崇拜”在今天的建筑学院确实存在,这种“pied-piperism”(借用埃里克·莫斯(Eric Moss)的一个术语)已经导致许多有前途的学生陷入了无用的领域。然而,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迷失的人最终会找到回家的路,而且他们回来时往往已经准备好将在国外领域获得的经验转化为在学科领域内的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彼得对数字技术的邪恶势力的抱怨既缺乏特殊性,也缺乏实质性内容。他只是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数字工具剥夺了创造力。他不仅不加评论地驳斥了几十年来全球各地学校的创新工作取得的明显成就,还驳斥了他自己的学生。更糟糕的是,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引用了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话,增添了一种老一辈人对新奇习惯的抱怨,而且,就像他引用巴尔代萨里一样,削弱了他对老一辈政治家的声明所赋予的不正当权威的告诫。
不管问题有多大,彼得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伤大雅的。我更担心他提出的改革建议。他的后工作室教育方案基于一种似是而非(如果常见的话)的对艺术和建筑的省略,以及一种荒唐(如果同样常见的话)的论点,即建筑“不能被教授”。这样的争论忽略了艺术和建筑之间的显著差异,并延续了对建筑实践和教育本质的破坏性神秘化。
我同意彼得的断言,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但与绘画、文学、音乐和其他艺术生产方式不同,它也是一种艺术职业有重大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还有纪律用文化野心来提升公众的想象力。后一个方面是建筑实践与建筑工艺的区别。前者区别于美术的生产。
Peter和我都对建筑有着深刻的承诺,将其理解为具有专业责任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具有文化野心的设计专业。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同意他的建议,尽管他对所谓的风格痴迷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但他仍然几乎只从美学的角度来描述建筑,只在“技术知识”上说上几句空话,过度强调风格和个人表达的问题,而忽视了专业能力的问题。任何关于建筑教育的严肃建议都必须全面考虑到建筑的专业和学科责任。
更有破坏性的是彼得的主张,也借鉴了巴尔代萨里,建筑不能教。显然,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设置一个[架构]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是由彼得·泽尔纳这样一位聪明而高效的老师提出的一个奇怪的想法。
彼得提出我们不能教建筑,因为他认为建筑,就像巴尔达萨里对艺术的看法一样,是一种神秘的品质,是物质转化为某种更高形式的存在。这就是彼得在他的文章中所抨击的那些学术巫师们口中经常涌出的那种东西。当然,这可能很诱人,但这是无稽之谈。
建筑不仅仅是发生.体系结构是使.建筑是可以建造的,它的方法是可以传授的,因为“建筑”指的不是一个特定的物体,而是一个物体——通常但不总是建筑——以特定的工作方式被制造出来的证据。正如文学不能简化为书籍一样,建筑也不能简化为建筑物。它也不能被简化为图纸、模型或数字动画。建筑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方法。《牛津英语词典》对建筑的定义不是建筑的一种,而是“建筑的艺术或科学”。另一位彼得,历史学家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说得更好:“建筑的区别在于不是什么完成了…但是如何就这么定了。”
理解建筑与如何而不是什么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建筑就像所有的学科一样,是一种文化建构。它的技术和方法,它的历史和理论,那些实践它的人的习惯和惯例,可以被常规地教授和学习,这一点从彼得在他的文章中哀叹的那些迅速掌握老师战术的学生的过剩中得到了证明。当然,这些技术、历史、习惯和惯例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开发、转换、抛弃和替换。这些活动是建筑学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以这种方式理解体系结构还可以更容易地看到该领域的价值系统,即它用于确定构成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内部方法,始终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建筑质量,就像建筑本身一样,不是由物体中某种准精神属性的存在与否决定的,而是由共识决定的。支持任何建筑工作的选区必须在项目可以建造之前就建立起来,即使建造的建筑物不是一个人的目标,它是一种聚集这些选区的能力,而不是其他能力,将个人兴趣转化为相关的贡献,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权威的成就。
换句话说,建筑的美学野心具有深刻的政治色彩。正如彼得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建筑教育的学科政治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丑陋的情况。幸运的是,当代建筑能够并且确实支持广泛的共存类型和相关的价值体系。在最好的学校里,少数人会争夺主导地位,激励每个人的支持者在阐述各自的观点、建立各自的支持者群体的同时,不断磨练自己的政治、美学和技术能力。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好心但被误导的教师会说出空洞的声明,比如“你不能教建筑”。
当今的当代建筑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我赞扬彼得将其中一些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但在建筑学院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最重要的肯定是许多教师放弃了他们教授建筑的责任。
托德·甘农(Todd Gannon)是SCI-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