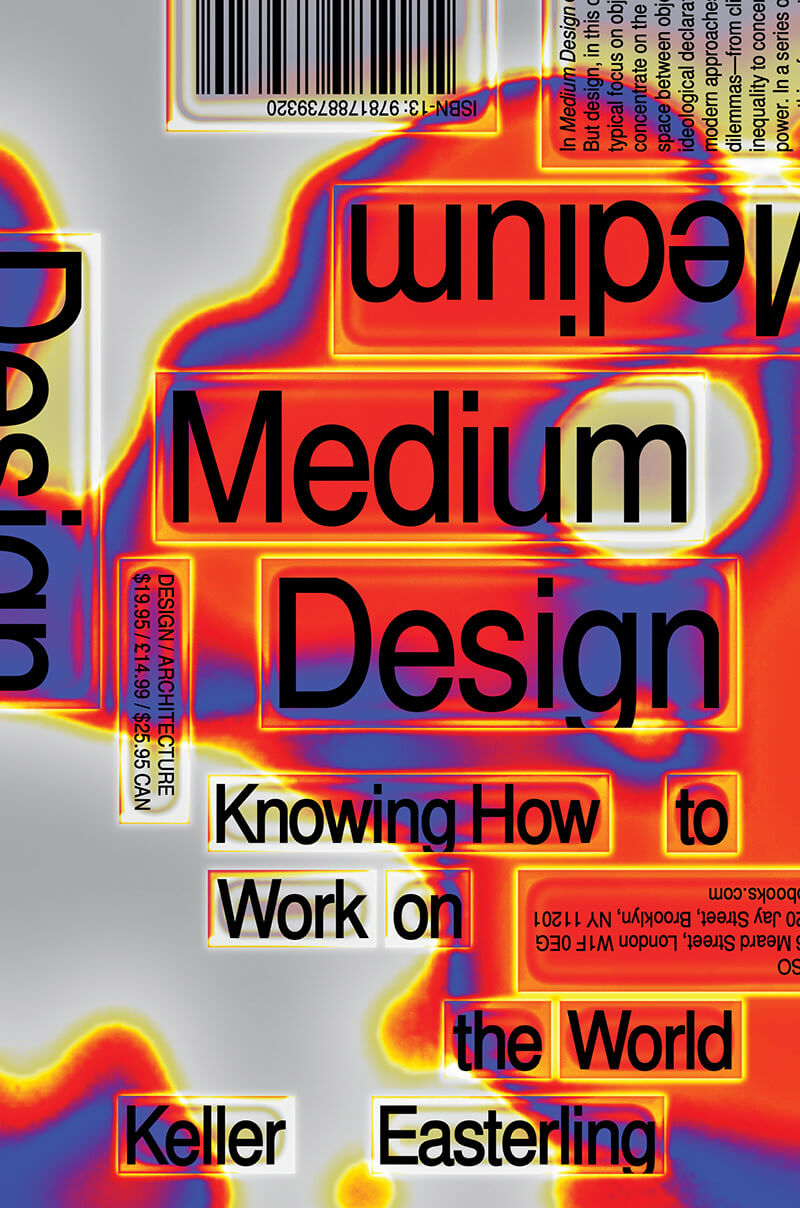媒体设计
凯勒东方国家的人
左页
厂商建议零售价:$ 20
必须明确的是:凯勒东方国家的人的媒体设计是一个宣言不管它多么抗拒这个标签。广义上讲,它的主题是设计师;这个人不仅仅是物品的生产者,他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专业证书,而只是拥有适当的风度。“(设计)工作不需要一个名字,”伊斯特林劝诫道,“而且你已经知道如何去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师改变了现实本身的“媒介”,现实被呈现为点缀着“活的”物体——从铅笔、电脑到火车、国家,甚至国际治理组织——这符合当今流行的技术泛灵论。但与此同时,伊斯特林的设计师仍然是一位专家:他们拥有超感官能力,使他们能够观察“像街道一样的城市空间,甚至在静态实体之间的关系中评估潜力。”世界在其本质上呼唤着被恰当地利用。如果这些墙会说话,它们就会乞求“媒介设计师”去激活它们的潜能和表现。然而,设计师不能直接对世界采取行动——这样做是规范性的。他们远离现实,进入抽象,而是设计相互作用,特殊的空间关系,可能执行某些“政治优势,权宜之计,和催化剂”的媒介设计师的代表。
就像任何好的宣言一样,媒体设计沉迷于政治伊斯特林,他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写了政治似乎这可以归结为拙劣的模仿或病态,总是一个“政治阵营固若木然,带着悲喜剧的咆哮,退回到意识形态的循环中”的案例。在这种狭隘,她给读者提供了开放式的场景设计是定义扩展到包括一切,和在表面上“非”意识形态的伪装,那些自由言论给出一个新的光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的诱人的词典的“超级细菌”,“开关”,“乘数效应”)。通过这样做,她创造了一个定制的理论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可以声称自己在提供常识性的建议。一个人必须工作在系统中通过这样做,不知何故逃避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导致了奇怪的扭曲,就像书中的几段插曲一样。例如,伊斯特林引用了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 1955年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设计活动,她“激活了一种未公开的城市配置”,并“改变了空间政治矩阵的潜力,打破了一个循环,而不加剧危险的二元性。”这句话的含义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在伊斯特林的诗文中,帕克斯的抗议不是战斗口号,而是一种“转变”,只是花了一点时间去思考,超越了白人至上主义本身。这种对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事件的解读认为,它(作为一种主权力量,一种相互作用)通过采用“一种令人惊讶而又不可能的叙事形式:一个没有冲突的故事”,努力将支持者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上。更准确地说,伊斯特林是在提倡历史没有冲突。以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就像在我们面前一样。没有必要再参与左右两派之间的消耗战,没有必要再去对抗巨大的“你的敌人,比如资本”,也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去纵容那些仍然相信革命或实质性变革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短视的希望者。由罗莎·帕克斯和其他介质的相互作用天才设计师喜欢她导致个体行为,避免政治僵局工作直接与空间,已经被剥夺了政治或其他,成为纯粹的内容“驾驶、劝诱、倾向或激活,形成更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其他地方,伊斯特林提供了一个稍微不那么令人困惑的相互作用的例子。否认总体规划和其他可能的“全面的解决方案(总是失败的),她找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替代联合国人居署的包容性土地调整方案皮拉尔。听她说,这个项目代表着一个激进的举动,它背离了古板的旧观念,即建筑物是根据其财务价值编入索引的私有财产。相反,“皮拉”推动创建“由若干参与者指导”的合作社,这些参与者管理的社区受到“与邻近性、流动性、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沉重价值观和功能支持”的约束。
与此相比,联合国人居署自己的城市土地调整报告更冷静地将“PILaR”描述为“自愿购买”和“与征用或土地征用相关的费用、漫长、昂贵和危险的法庭斗争”的第三种选择,威胁要吓跑开发商,或阻挠地方和市政当局为他们的利益所作的努力。换句话说,“PILaR”和类似的土地调整举措是帮助减轻开发成本的方法。但伊斯特林被委婉的“调整”承诺所吸引,她将其解释为一种积极的途径,“允许一个不起眼的社区彻底改造他们现有的房产”。她甚至声称过程”可能会让许多人摆脱单纯依赖的precarity工资,“通过重塑成员合作的地主或建议而不是“[t]他居住的位于价值是他们沉重的投资组合在一个空间marketplace-a物理,有形的价值。”联合国人居署官员如果想强调土地调整的“包容性”,就会对这一光辉的解释感到自豪。
媒介设计师凌驾于政治和经济的琐碎斗争之上的假定地位是基于设计师的另一个独特能力:经验诀窍。这是设计师“展开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命令,允许他们“在社会、政治、金融和空间环境经济中锻炼自己的积极能力”。设计师牧师(和他们自己)的隐性知识可能会识别“空间中的任何功能可见性……由无法货币化的活动或邻近物构成。”但是,钱的持续存在时时刻刻困扰着这些活动。要相信伊斯特林有新的见解,首先需要读者忘记私人财产的存在,并不是设计者在指挥它,而是财产的拥有者——无论是空间上的,财务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关于正确知识的好论点从来没有说服所有者放弃他们的财产,热心的地主也不会对“更伟大的利益”的召唤做出典型的回应。
伊斯特林在第三章的扩展场景中对比了“知道如何做”和“知道如何做”。她告诉我们,聪明也可能是愚蠢的,因为它具有规范性的解决方案主义。因此,自动驾驶汽车虽然被支持者称为“交通运输的灵丹妙药”,但最终还是会重现以汽车为中心的“单价”网络带来的拥堵、蔓延和其他连锁效应。她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来打破这个概念循环:一个卧室社区的服务不足的火车站通过引入一组自动驾驶汽车而投入使用;似乎一夜之间,这个车站变成了一个多功能枢纽,吸引了多种交通方式——自行车和高速铁路——并引发了郊区结构和行为模式的变化。这是书中较为乐观的场景之一,让人们重新相信“开关”,即设计师的愿景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神奇时刻。“他的相互作用,”伊斯特林说,成为了“组织资本和政治的强大空间引擎或差异,而不是反过来。”
设计师的任务仅仅是召集相互作用,然后将控制权交给处理程序组织的“多个玩家”,以防止“仅由数据或金钱解析”正在展开的情况。但通过将责任推卸到具体化的“相互作用”上,设计师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任何由他们的行为引起的负面影响。然而,问题仍然存在:这些空间变化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
建筑不是流动的,私人财产也只有最低限度的可塑性。声称该转变具有“在不宣布(任何)政治倾向的情况下改变布局”的权力,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重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火药桶,即使是引入一条新的交通线路或车站的简单举措,也经常会遇到当地的激烈抵制,更不用说美国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尤其惨淡的现实,估计有2万亿美元的维修积压。假装一个人可以从设计的前沿阵营指挥政治或经济,最终会沦为一种劝诫,认为只有最好的意图才重要,即使它们破裂了。
最后,我们到达媒体设计最重要的盲点:权力。在书的最后,伊斯特林困惑地评论道,“泳池玩家、骑自行车的人、小丑、狗、化学家、厨师和父母的隐性知识/媒介设计”并没有应用于“影响解决世界上最困难困境的方法”。她假装的一种近乎平易近人的敢做敢做的态度——因此任何东西都可以并且应该回应媒体设计师的“文化肌肉记忆”——基于她公开宣称的“不存在一个包罗一切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有的权力和暴力都源于此”。这对于实现书中的目标是必要的——让设计师成为唯利是图的人。有权势的人物和机构,甚至是专制的机构,都可以被精心设计的手段颠覆;我们只需要先锁定委员会。当伊斯特林指出媒介设计师的角色类似于父母处理不守规矩的孩子或台球选手排队击球时,她实际上是在暗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幼稚的政治分歧争吵。如果在这项工作中发现了真正的心跳,那就是对任何定罪的自以为是的蔑视。
伊斯特林的媒介设计师既不是家长,也不是赌徒,更不是有原则的活动家。相反,他们是梦想拥有天堂车床的官员。媒体设计这本书是写给这些正在等待时机的优秀员工的一种缓和药,并以一种自助的方式,通过提供伪装成常识的荒谬梦想来安慰他们。伊斯特林写道,“甚至有可能是被资本丢弃或忽视的土地拥有获得设计价值的最大机会,”但什么样的土地符合这种描述?地球上有什么碎片不是属于你的?没有。媒介设计师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资本执行计划,而设计师必须像往常一样随波逐流。这本书是为那些想在早上忘记工作的人准备的睡前故事。
凯文·罗根(Kevin Rogan)是一位作家、设计师、学生和业余爱好者,住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