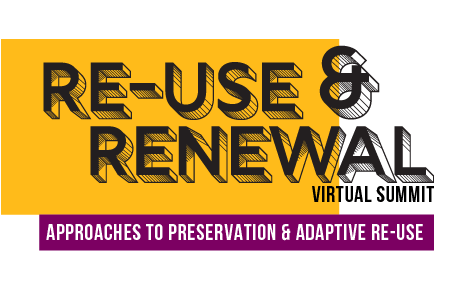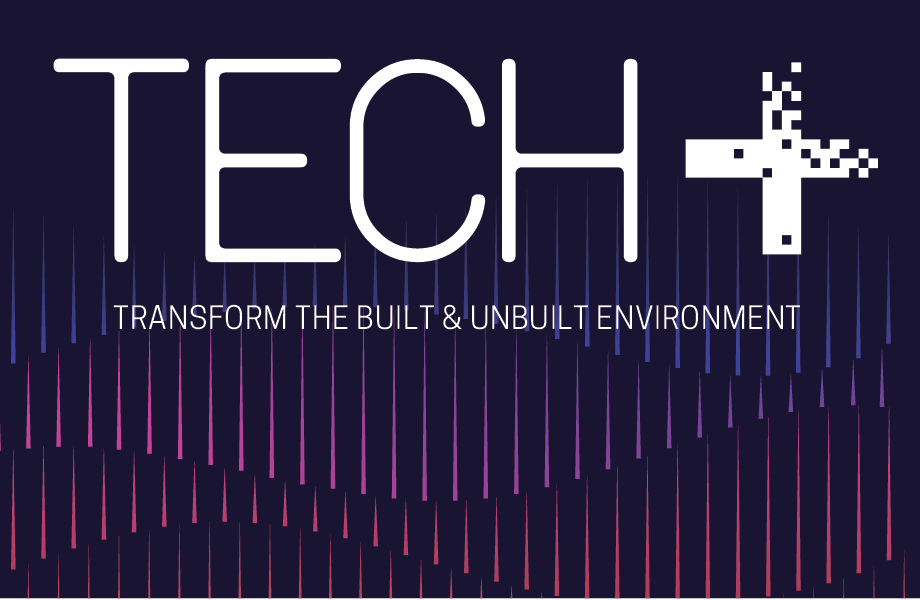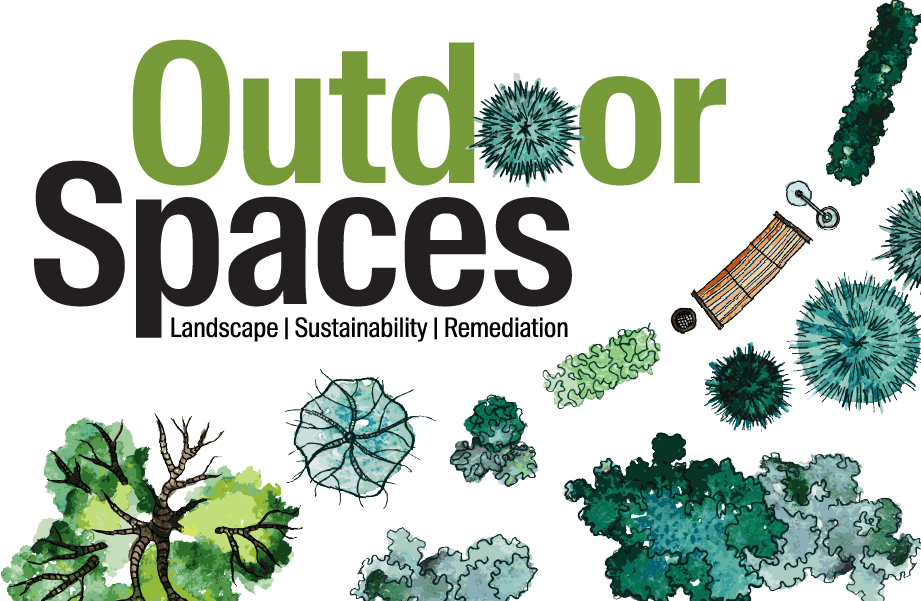迈克尔索金独一无二的建筑环境和领先的设计思想,去世了他于上周四在纽约感染了COVID-19,享年71岁。索尔金的妻子琼·科普杰克去世后,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作品在悼念——来自朋友、同事、同行——欣然承认。这是两部分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种是可以阅读的在这里.
埃里克·欧文·莫斯校长,Eric Owen Moss建筑事务所:
迈克尔•索尔金
你在哪里?
看不见的东西。
忠于这一事业。
评论家迈克尔。
迈克尔,城市规划师。
迈克尔,政治辩论家。
迈克尔是建筑师。
讽刺的幽默家迈克尔。
无家可归,家里到处都是。
教育教育者。
同事的定义。
朋友的定义。
重新绘制批评家、城市学家、警察和建筑师的地图。
永久。
因此,拖欠债务的国家可以效仿。
如果他们可以的话。
迈克尔,你在哪儿?
在罗莎吃饭?
一起嘲笑首席芭蕾舞演员和四分卫?
有人曾经告诉我们,“太阳也会升起。”
只是不是今天。
爱你。
汤姆·梅恩、创始合伙人Morphosis Architects:
在八十年代我们都在挨饿的时候,迈克尔会把我安排在他的公寓里,我坐在一张令人难忘的Pesce Feltri椅子上,我们聊着我们都喜欢的话题——建筑,聊到深夜。我精疲力竭地躺在椅子的两翼上,睡了一觉,然后醒来,就好像没有时间过去一样,我们又开始了。他的声音,就像昨天一样,尖锐、无畏,有时还尖刻。他反复用我不想听的话挑战我。但我相信他——他的评论显然来自一种慷慨、诚实和对他的项目的承诺,这个项目最终是关于社会公正的。
他谈到我们的重大责任,他毫不留情地谈到建筑改变生活的力量,他从未停止坚持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停止战斗——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对现状的反抗。他惊人的智慧加上他对人类的明显热爱,使他的文字具有罕见的庄严和力量。最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想起那间屋子,那把椅子,那段时间,我意识到,是与人沟通的礼物让迈克尔如此特别。我在想那把椅子,那些时光,那颗心,而我,就像过去几天里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一样,毫无头绪,感觉迷失在悲伤的迷雾中,我找不到边缘。
史蒂文·霍尔校长,Steven Holl建筑事务所:
迈克尔·索尔金被新冠肺炎夺去生命的悲惨消息令人难以置信——悲剧的超现实。我认识迈克尔有四十多年了。我刚到纽约的时候,他邀请我参加新年前夜的一个活动。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具有深邃智慧和敏锐智慧的建筑师。他是卓越城市愿景的拥护者,就像我们的好朋友莱伯乌斯·伍兹(Lebbeus Woods)一样,他对建筑有着无畏的信念。
迈克尔和塞万提斯的角色很像堂吉诃德以最好的方式。我记得他说过:“我可能无法实现我所有的梦想,但我会为之而死。”让我们关注这个人类的悲剧时刻。正如Malebranche所说,“注意力是灵魂的自然祈祷。”

Gans工作室创始负责人Deborah Gans:
我一直在回想迈克尔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反应,无论是迫在眉睫的还是隐现的,卡特里娜飓风和耶路撒冷,气候变化和全球暴力。总是有尖锐的文本,揭露了他们的伦理要求和他们对建筑和规划的物理后果的艰难真相。但是,最常见的是一份草拟的提议,充满活力,为我们的出路。他是一个二元的人——既致力于乐观主义,又致力于对抗不公;既快乐于他的存在,又风趣于他的智慧。
通过他的作品,我们了解了新奥尔良的不稳定;但是,通过他对居住堤防社区的灵感设计,我们看到了希望。他用晶莹剔透的文笔描绘了巴以僵局中伦理上的愚蠢行为,讲述了苦难、所有权、环境管理、神圣、侨民和国籍等相互矛盾的故事;但接着,在标志性的粉色计划中,他想象在东耶路撒冷建造一座绿色的巴勒斯坦新首都,我们不禁问自己:“为什么不呢?”
现在,我们需要他来帮助我们解开“遥远的城市主义”和“基本服务城市”的修辞,以及夺去他生命的那场瘟疫的所有政治层面。我们还需要他给我们的计划在这场洪水之后夺回我们的城市。对于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是绿色的、民主的、快乐的。
景观设计师Achva Benzinberg Stein:
“亲爱的,”迈克尔经常对我说,“别抱怨了,开始工作吧。”他总是这么做。尽其所能地努力生活,通过指导和鼓励来教学,打开我们的思维,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来实现它们,用他独特的语言非常雄辩地写作,带有细微差别,词汇丰富,证明了他在许多领域的渊博知识。
1994年我们见过一次面,当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推测性的。但他相信一个好概念的力量可以说服人们采取行动。如果需要钱来支付那些依赖他的助手们的工资,那就毫无疑问该怎么办了。“大玲,你会看到一切迟早都会被覆盖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
这就是他的设计方式,玩弄物品和形式,从不害怕尝试或承认失败,用难以置信的幽默,带着对人的爱,带着深切的关心和对这个城市的集体潜力的坚定信念,为任何进入他脑海的问题发明解决方案。
再见了,我的灵魂兄弟。我非常想你。
莱斯利·洛克,院长伯纳德和安妮斯皮策建筑学院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就在十年前,我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会议上短暂地见过迈克尔·索金一次。那是在一场活动结束后的晚宴上,每个人都见面了,谈话很简短。我有点追星族的感觉。我们没有交换联系方式,也没有再联系过。九年后,他提名我为城市学院斯皮策建筑学院的新院长。就像我们在西非所说的那样,在我“坐在座位上”的短短三个月里,我们在教师会议上或偶尔在走廊上见过几次面。三周前,他迅速组织了一次与以色列电影制作人阿莫斯·基泰(Amos Gitai)的晚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顺便提到,我是他作品的超级粉丝。“我会叫你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做到了。这是一顿精彩的晚餐,迈克尔虽然“戒酒了”,但招待得很好。 I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通过过去几天里涌入我收件箱的悼词,我现在明白了,慷慨、敏锐,以及培养和保持这么多分散在各地、互不相干的人的信任、爱戴和尊重的巨大社交能力,不仅是他的标志,而且是他的标志是这个男人。它是一个cliché,但是,和大多数clichés一样,它植根于事实:只有当你失去时,你才会意识到你所拥有的。

哈丽特·哈里斯,院长普拉特建筑学院:
幸运的是,难相处的人没有轻松的话可说;他挑战建筑师培养一些众所周知的道德规范,为他人挺身而出,甚至为自己挺身而出,抵制肆无忌惮的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犯罪。
我会记住迈克尔,因为他允许我和其他人将建筑作为一种充满诗意的、社会抗议的形式。事实上,很少有教育工作者这样做过。我不会忘记我欠他的。他对那些使人衰弱的传统教条的不耐烦,给我们的谈话增添了活力,扰乱了辩论,也使他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否则,学生们就会被压在隔离实践与学术的带电栅栏前。
迈克尔坚持认为,关于建筑,我们所有建筑师都应该知道250件事,但关于迈克尔,也许只有一件事需要知道:没有他,我们的社区将大大缩小。
迈克·戴维斯,作家、活动家和城市理论家:
迈克尔·索尔金今天在一家人满为患的医院因冠状病毒去世,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损失。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城市理论家”,那只是因为1992年迈克尔征召我为他的《主题公园变奏曲》一书写一章。他的思想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如何,他都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城市生活和建筑的激进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当他还是《乡村之声》的建筑评论家时,足够年长的纽约人就已经是《乡村之声》的读者,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超级开发商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城市强奸犯发动的战争。或者他如何用惠特曼式的散文每周唱纽约不守规矩的民主街道的民谣。
当后现代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尸体上撒土时,迈克尔正在复兴社会主义梦想和自由主义乌托邦,这是建筑现代主义的原始灵魂。当人民的城市遭到攻击时,他不可避免地是第一个在枪炮声中前进的人。然后…,他的魔鬼般的欢乐,他的善良,他飙升的想象力,他5万伏的创造力....我的键盘被泪水淹没了。
迈克尔,你这个叛徒,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走了?
Dean MacCannell,环境设计与景观建筑学名誉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死亡突然把迈克尔·索金从我们身边夺走。但我们不能让他走。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介入太多了。有太多的依恋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撤消它们。
迈克尔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不仅仅是那些有幸参加他的研讨会和工作室的人。当他要求我解决我所不了解的问题时——他经常这样做——他总是忽视我的无知,要求我和他一起工作。他是一个超越建筑的建筑师。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创造机会,把我完全吸引到他的计划中来。迈克尔在许多领域和学科上都学识渊博,但他把自己的学识轻描淡写,并以一种邪恶的幽默感战略性地运用它。他写得很优美,使我们的意识在瞬间形成。
迈克尔抛弃了他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憧憬——创造性地重新想象。我们其他人未完成的工作,以及完成它的必要工具:对人性不可动摇的信心;我们的自治能力;我们实现其他启蒙理想的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基础。
谢谢你,迈克尔。我们会尽力的,但该死的,如果你还在这里指导我们就容易多了。

埃亚尔·魏茨曼,创始董事法医架构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空间与视觉文化教授:
我被锁在目瞪口呆、无助的隔离室里,出口标志被关闭,我听说迈克尔去世了,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道别。当代公共空间和城市欢乐的先知死于一家医院——这是最后几个仍然可以,甚至不可避免地进行身体接触的地方之一。这种病毒代表了迈克尔在一个几乎完全关闭的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所倡导的那种社会互动,人类接触的代价变得太高了。
那天晚上,当可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伦敦附近的人们,寻求某种形式的交流,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窗口,为医疗工作者鼓掌,就像那些在迈克尔最后的日子里陪伴在他身边的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挽救他和我们的生命。
迈克尔是我们家的朋友——我的女儿阿尔玛被他的女儿宠坏了——所以我们站在窗前,一边抽泣,一边鼓掌,一边用木勺敲打着锅,为迈克尔举行我们认为他会喜欢的送别仪式。剩下的哀悼必须在隔离中进行——我的心与琼同在,她无法从那些深爱着他们的人的身边受益。
迈克尔还是我的建筑教父。通过一系列小而关键的纠正措施,他让我走上了正轨。他在我的书还在草稿的时候就看了,给我评论,帮我找书名和出版商。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还抽出时间为我助选,当时我还不能去美国,就像他经常为其他不那么有特权的人做的那样。
我们是1994年认识的,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仰慕学生建筑协会(AA)我是为他竞选学校新校长的人之一。当迈克尔最终赢得投票并得到这个职位时,他决定拒绝这个职位,而是选择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成立了研究机构Terreform和出版公司UR (Urban research);并成为城市学院的研究生设计主任,在那里他是特聘教授。简而言之,他自己构建了一个多态的实体,通过它来实现他广阔的城市愿景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他继续在一系列的文章和书籍中宣扬他的想法,并在无数富有远见的方案和图纸中勾勒出这些想法。(后者的很多书还没有出版,但琼向我保证它们很快就会出版。)
利用20世纪70年代纽约激进主义的词汇,他扩展了建筑和城市行动的范围:静坐、市政厅会议、请愿、上诉、法典和权利法案的撰写。从他与现在掌控美国的纽约开发商的斗争中,他把自己的城市正义感和活跃的行动主义带到了巴勒斯坦、北爱尔兰和美墨边境。由于建筑是问题的一部分,它欠了一定的债务,迈克尔鼓励建筑师通过发明解决方案来还债。
1998年,作为一个顽皮的骗子,迈克尔引诱了一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建筑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在意大利贝拉吉奥的湖边别墅参加了一个关于被占领和被隔离的耶路撒冷的会议。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Suad Amiry, Rashid Khalidi, Omar Yusuf和Ariella Azoulay。我们一起听着,迈克尔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乐观地坚持说,我们可以用建筑来为这种不公正做点什么,尽管他明白,如果不伴随着我们都必须为之奋斗的根本政治变革,建筑本身就做不了什么。他后来的书是关于巴勒斯坦的下一个耶路撒冷,靠着墙,开放加沙-说明他的意思。
他是对的,当建筑对我们的控制越来越紧的时候,当墙、塔和数字监控系统的建造者掌握大权的时候,当威权主义者利用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侵犯我们的公民自由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引导迈克尔的一些东西,继续战斗。他现在要把他的东西带给众神和天使。继续,迈克尔,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纽约大学社会和文化分析教授安德鲁·罗斯说:
当我在80年代末搬到纽约时,我养成了通过迈克尔的眼睛看这座城市的习惯,我想我永远都会这样。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特的批评家,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实干家,这一点我特别钦佩。
我们以各种方式合作,但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两个比赛的评审团。第一个是与亚特兰大奥运会有关的公共空间项目。迈克尔为自己的选择游说其他评审团成员时那种咄咄逼人的魅力赢得了我的好感。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他的帮凶,我们全心投入最大胆的项目,我们很清楚,在现实世界中,这些项目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小。
许多年后,我们都有了独立的想法,为拟议的竞争建立一个替代方案古根海姆赫尔辛基,所以我们携起手来坚持到底.从全世界公司的纯支出来看,官方竞争是有史以来劳动密集型和成本最高的。一场真正的虚荣之火。我们的预算是5000欧元,运作起来更像一个智库,为艺术和都市主义注入灵感。整件事展现了迈克尔最好的一面——他对建筑精英主义的强烈厌恶,他对大众品质的渴望,他自发的同情心,是的,还有他传奇般的恶作剧意识,现在不幸地消失了。
丹尼尔·蒙克,乔治·r·和迈拉·t·库利科尔盖特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主任:
迈克尔·索尔金上周去世时,留下了一部作品的草稿即将出版的文集纪念我们一起编辑的迈克·戴维斯。在书中,迈克尔记录了他自己第一次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购物中心的遭遇。在这些关于“美国集市”的记忆中,他展示了购物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相当于对其承诺的永久背叛。如果说,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迈克尔在面对绝望时总能采取希望、幽默和恶作剧的立场,那是因为他知道这正是正确的破碎的承诺一种监管的理想——他一直拥护的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将继续存在,尽管我们集体努力闭上眼睛假装不这么做。
查尔斯Waldheim他是哈佛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约翰·e·欧文设计研究生院:
我很幸运地认识迈克尔·索金,他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是我的个人榜样,也是我的朋友。他的离去给这座城市的中心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也给我们这些致力于理解它的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迈克尔以记者的眼光和评论家的诙谐风趣来描写这座城市,把它描述为一个集体的社会结构和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他富有洞察力的散文穿透了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层层积累。他对介入城市的设计主张充满想象力,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批评的形式,揭示了权力结构、阶级建设和集体抵抗的考古。
大多数当代关于城市设计的论述已经萎缩为两种相互排斥且最终不充分的叙述之一。一方面,我们对城市的讨论退化为对政策、参与和治理的专属关注,与城市的空间和文化背景脱节。另一方面,我们的描述同样常常局限于对单个站点、项目和主角的描述,因为这些建筑奇点与集体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联系。将这座城市描述为一个集体文化项目是迈克尔·索尔金送给我们的伟大礼物。现在我们中间谁来做那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