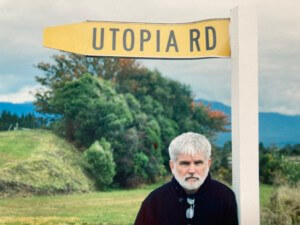建筑师报(AN)曾与urbanNext-一个多学科的设计平台Actar出版商-每两周分享一次关于共同话题的文章。
这周,我们配对urbanNext文章如下一个的”城市如何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以下文章的作者是亚历杭德罗Zaera-Polo他是伦敦/苏黎世/普林斯顿Alejandro Zaera-Polo and Maider Llaguno Architecture (AZPML)的联合创始人。
自18世纪西方世界以人为中心以来,人类一直在进化,人的概念也一直在进化。在1933年,勒·柯布西耶和CIAM的其他几个成员发布了《雅典宪章》,这是一份旨在将建筑环境的新兴技术整合为城市未来的建议的文件。[1]人类活动的分类成为这个提案的核心,围绕着四个城市功能:工作、居住、休闲和交通。从那时起,这种功能分类就构成了城市规划政策,但这种以人为本的方法现在似乎无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在人类世,人类已经有能力改变自然生态系统、地质结构,甚至气候;我们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越来越难以将自然与人为区分开来。作为人口最多的人类环境,城市是这些转变的中心焦点,然而,这些担忧似乎都没有渗透到我们用来规划城市的工具中。城市规划学科仍然主要围绕着人的功能来构思,尽管它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空气污染、水位上升、干旱、热岛效应、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自动化工作、不平等……——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人们的担忧所驱动的,这些担忧在历史上首次超越了人类社会,并威胁到地球的生存。现代城市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驱动力——生产、就业和消费的大规模整合;工作、居住、娱乐和交通的分离;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划分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今城市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同样地,传统的城市工具,如广场、街道和社区,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实践商品化,在处理新的城市集体和选民时变得无效,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它们充斥着当代城市。
城市在人类世建设中的作用已经不能再被忽视了。我们正在协助进行一场真正的范式变革,这需要重新定义构建当代城市主义工具所依据的宇宙观。城市的神秘技术和仪式通常是基于神话的参考。古代宇宙论是理解自然世界的机制,它使文化能够理解自然环境并在自然环境中运作。最古老的是在人类定居之前,旨在解释自然现象,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随着城市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机构的控制,作为城市知识和治理系统的宇宙论被抛弃了。类型学和纪念性成为主要的工具都市生活人类关系的结构凌驾于环境的物理和物质决定之上。的城市事务(politika)变成了一种完全人为的努力。目前普遍存在的人工环境和政治——城市——倾向于将技术自然化,同时将自然去政治化。然而,生态问题的紧迫性质和技术发展的规模要求即将到来的城市重新将自然和技术政治化,并构建新的城市宇宙观,以支持新的城市敏感性的发展。一套全新的城市技术已经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协议和体验:智能手机、GPS、电动汽车和生物技术。然而,这些技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的实践范围,他们仍然被困在现代城市主义的人文戒律中。城市功能主义非但没有产生城市化,反而消解了下议院破坏了城市民主。Clichés,例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社区和城市民主的保障的相关性,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无法量化密度和城市形式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或城市微气候的决定一样成问题。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可以在人类功能(如工作和家庭)的分配中找到有效的代理的想法充其量是naïve。城市已经成为极端不平等和环境退化的根源(这不仅是对社会的蔑视演示这些甚至威胁到城市的生存,并指出当前经济一体化模式的核心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保罗·梅森(Paul Mason)等理论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正从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关注转向对能源和资源的关注,他们提出了新的经济:由新技术推动的零边际成本共享经济:由普惠计算、可持续能源和碳中性技术增强的点对点组织。[2]
作为人类最大的栖息地,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变暖、空气污染和各种生态问题的中心。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指出了资本主义增长与地球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根本对立,并质疑资本主义政权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的能力。[3]资本主义的衰落给城市生态和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意义。城市现在已经成为生态、技术和政治之间的重要交汇点,财富、劳动力、资源和能源之间的等式必须重新设定,以解决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缺点。
生态和技术,而不是功能
这种由人类世的兴起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所决定的情景,是否意味着城市规划学家和建筑师的工作已经变得徒劳?新公地将完全在社交媒体中发展?城市化是否已被驱逐出政治,现在是否受证券化和资本再分配的摆布?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4]认为城市规划、住房和房地产是解决城市不平等的关键。[5]城市先于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在系统上比政治制度存在得更久,往往构成了对权力的抵抗机制。为了让城市成为公共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产生和实施权力结构(通常是不平等或生态破坏)的工具,城市实践需要将资源和技术置于其核心位置。我们不应该把城市生活划分为容易被权力掌握的功能,而是应该首先努力确定权力在哪里迫在眉睫的城市公地是和如何重建它们作为权力下放和生态意识的工具,跨越技术和资源横向构建。我们试图勾勒出这些可能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成为修订城市实践的来源。
本文最初发表于迫在眉睫的城市公地在urbanNext。
[1]勒·柯布西耶、让·吉拉杜和让娜·德·维伦纽瓦,《雅典宪章》(巴黎:普隆,1943)。
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物联网、协同公地和资本主义的衰落》(伦敦:麦克米伦,2014年。保罗·梅森,《后资本主义:我们未来的指南》(伦敦:Allen Lane出版社,2015年);保罗·梅森,《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开始》,《卫报》,2015年7月17日,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17/postcapitalism-end-of-capitalism-begun。
娜奥米·克莱因:《这改变了一切:资本主义与气候》(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
[4] Matthew Rognlie,“解读净资本份额的下降和上升”,BPEA会议草案,2015年3月19日至20日;http://www.brookings.edu/~/media/projects/bpea/spring-2015/2015a_rognlie.pdf, 2016年10月5日访问。
[5]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剑桥,马萨诸塞州:贝尔纳普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印记,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