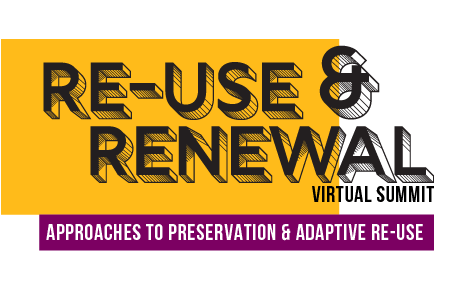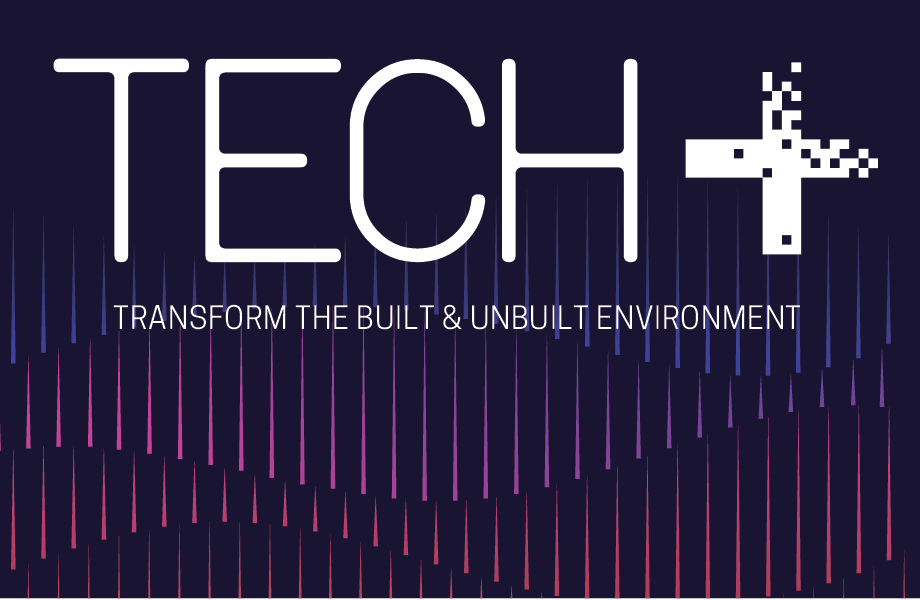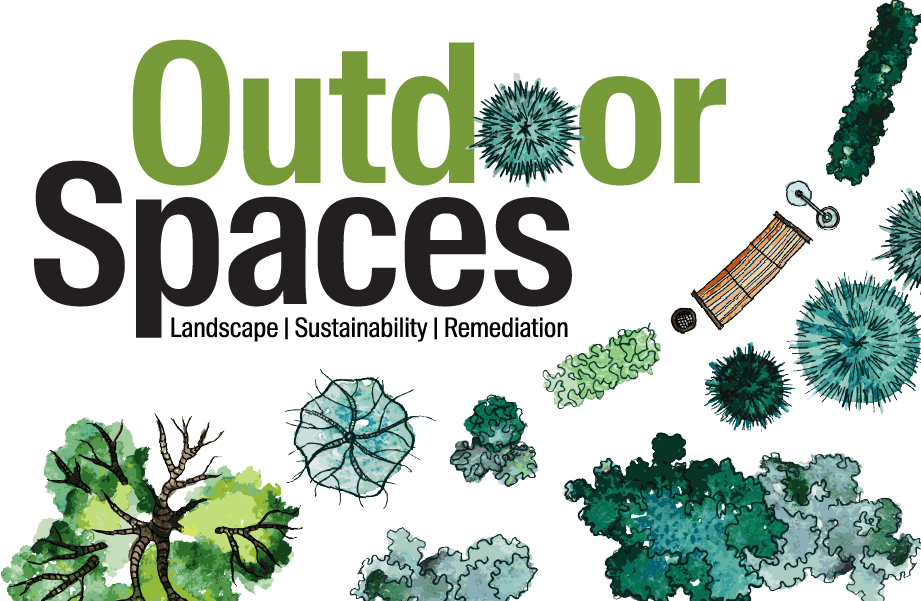1910年,在巴尔的摩,一名耶鲁法学院的黑人毕业生在一个以前全是白人的社区买了一套房子。巴尔的摩市政府的反应是通过住宅隔离条例将非裔美国人限制在指定街区。巴尔的摩市长在解释这项政策时宣称,“黑人应该被隔离在孤立的贫民窟里,以减少内乱的发生率,防止传染病传播到附近的白人社区,并保护占多数的白人的财产价值。”
一个世纪以来,联邦、州和地方的政策将巴尔的摩的黑人隔离在孤立的贫民窟中,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联邦住房补贴政策仍然不成比例地起到直接作用低收入的黑人家庭将居民区分开远离中产阶级郊区。
每当年轻的黑人男子因警察的暴行或谋杀而暴动时,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警察素质——训练警官不要过度使用武力、实施社区警务、鼓励警察更加敏感、禁止种族定性等等——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好的、必要的、重要的事情。但这样的提议忽略了一个明显的现实,即抗议活动实际上(或主要)与警察无关。
1968年,在全国发生了数百起类似的骚乱之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隔离和不平等的社会”,“种族隔离和贫困在种族隔离区创造了一种大多数美国白人完全不知道的破坏性环境。”克纳委员会(由伊利诺斯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补充说:“美国白人从来没有完全理解的——但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白人社会与犹太区有着深刻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它,白人机构维持着它,白人社会纵容着它。”
在过去的50年里,这两个社会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尽管一个相对较小的黑人中产阶级被允许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那些被抛弃的人却被允许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现在更多的种族隔离比1968年的水平高。
当科纳委员会指责“白人社会”和“白人机构”时,它使用了委婉的说法,以避免指名道姓地说出当时所有人都知道的罪魁祸首。这不是一个模糊的白人社会创造了贫民区,而是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明确雇佣种族法律、政策和法规以确保美国黑人将生活在贫困中,并与白人分开。巴尔的摩的贫民区不是由个人歧视、收入差异、个人偏好或人口趋势造成的,而是由政府违反第五、十三和十四修正案而采取的有目的的行动造成的。这些违反宪法的行为从未得到补救,我们正在为我们不断看到的暴力付出代价。
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杀害迈克尔·布朗后,我写道:弗格森的形成这段历史是圣路易斯县政府支持的种族隔离,为当地警察和社区之间的敌意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圣路易斯奉行的每一项明确的联邦、州和地方种族隔离政策,都与巴尔的摩政府奉行的政策有相似之处。
191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巴尔的摩1910年的种族隔离规定等条例违宪,不是因为它们剥夺了非裔美国人居住在他们负担得起的地方的权利,而是因为它们限制了(白人)房主的财产权,限制了他们愿意把房子卖给谁就卖给谁。巴尔的摩市长的回应是,指示城市建筑检查员和卫生部门调查人员,揪出任何在白人为主的社区向黑人出租或出售房屋的人。五年后,下一任巴尔的摩市长通过成立了一个正式的种族隔离委员会并任命城市律师领导它。该委员会协调建筑和卫生部门与房地产业和白人社区组织的努力,对任何试图向黑人出售或出租房屋的白人施加压力。例如,该市房地产委员会的成员陪同建筑和卫生检查员,警告业主不要违反该市的肤色界限。
1925年,巴尔的摩的18个社区协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公民与保护联盟”,目的是敦促新业主和现有业主签署限制性契约,承诺业主永远不把房子卖给非洲裔美国人。如果邻居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要求法院驱逐违规购买房产的非裔美国家庭来执行契约。限制性契约不仅仅是房主之间的私人协议;他们经常受到政府的制裁。在巴尔的摩,由市政府发起的种族隔离委员会(Committee on isolation)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了可以传播和执行此类契约的社区协会。
作为契约的补充,非裔美国人被禁止搬到白人社区联邦房屋管理局(FHA)的明确政策该法案禁止郊区住宅区的开发商获得联邦政府补贴的建筑贷款,除非开发商承诺将非裔美国人排除在社区之外。联邦住房管理局还禁止非裔美国人自己为购买住房获得银行抵押贷款,即使是在郊区,这些住房是在没有联邦建设贷款担保的情况下由私人融资的。联邦住房管理局不仅拒绝为白人社区的黑人家庭提供抵押贷款保险,还拒绝为黑人社区的抵押贷款提供保险——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红线”,因为在政府地图上,社区被涂成红色,表明这些社区应该被视为信用风险低的社区,因为非裔美国人居住在这些社区(甚至附近)。
由于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又被限制在住房供应短缺的拥挤社区,非裔美国人要么以比白人社区类似住房高得多的租金租房,要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房。这些安排被称为合同销售,与抵押贷款不同,因为每月的付款是不分期偿还的,所以一次拖欠付款就意味着失去一套房子,没有积累的股本。在大西洋去年,Ta-Nehisi Coates描述了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在芝加哥。在总结她的书时,家庭属性罗格斯大学历史学家贝里尔·赛特说这样描述它:
因为黑人合同买家知道他们很容易失去他们的房子,他们努力支付膨胀的月供。丈夫和妻子都是两班倒。他们忽视了基本的维护。他们把自己的公寓细分,塞进额外的房客,只要有可能,就向房客收取高额租金。
白人注意到他们的新黑人邻居过于拥挤,忽视了他们的财产。拥挤的社区意味着拥挤的学校;在芝加哥,校方采取了“双班制”的应对措施(一半在上午上课,一半在下午上课)。孩子们被剥夺了一整天的上学时间,只能在放学后自己照料自己。这些条件助长了帮派的兴起,反过来又使店主和居民惊恐不已。
最终,白人逃离了这些社区,不仅因为黑人家庭的涌入,还因为他们对过度拥挤、学校衰败和犯罪感到不安。他们也明白,他们住得越久,他们的财产就越不值钱。但是黑人合同买家在他们的房产全部付清之前没有离开衰落社区的选择——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失去迄今为止在该房产上的所有投资。白人可以离开,黑人必须留下。
合同购买制度在巴尔的摩很普遍。它的存在完全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政策,拒绝向黑人或白人社区的非裔美国人提供抵押贷款。
在全国范围内,黑人家庭收入目前约为白人家庭收入的60%,但黑人家庭财富仅为白人家庭财富的5%左右。在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非裔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家庭的困境几乎完全归因于联邦政策,即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郊区繁荣时期,禁止黑人家庭积累住房资产,因此禁止黑人家庭像郊区白人那样将这些财富遗赠给子孙后代。
正如我在《弗格森的使,联邦政府维持了一项政策公营房屋的种族隔离全国几十年了。无论是在纽约这样的东北部城市,还是在巴尔的摩和圣路易斯这样的边境城市,情况都是如此。1994年,民权组织起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声称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在巴尔的摩的公共住房实行种族隔离然后,在把最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家庭集中在最贫穷社区的项目中之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和巴尔的摩市拆除了这些项目,并有意将以前的居民安置到其他隔离的黑人社区。最终的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向前公共住房居民提供在融合社区居住的住房券,并通过咨询和社会服务来支持这一规定,以确保家庭搬到融合社区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尽管该项目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典范,但它只影响了一小部分家庭,并没有实质性地拆除巴尔的摩的黑人贫民区。
1970年,他宣布联邦政府已经在巴尔的摩和其他城市的贫民区建立了“白色套索”,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乔治·罗姆尼提议拒绝为下水道提供联邦资金或重新开发到全是白人的郊区,这些郊区通过维持排斥性分区条例(禁止多单元建筑)或拒绝接受补贴的中等收入或公共低收入住房,抵制融合。在巴尔的摩县的案例中,由于该县的居住隔离政策,他取消了一笔之前承诺的下水道拨款。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举动,但罗姆尼得到了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支持。阿格纽在担任巴尔的摩县行政长官和马里兰州州长时,曾因郊区对融合和混合收入发展的不合理抵制而感到沮丧。1970年,阿格纽在对全国商人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merchants)的一次演讲中,抨击了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向市中心投入大量资金来解决国家种族问题的做法。阿格纽说,他坚决反对这样一种假设:“因为种族和贫困的主要问题存在于美国城市的贫民区,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必须在那里找到……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所需的资源在郊区地区有大量的供应,但没有充分利用来解决内城问题。”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最终限制了罗姆尼,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整合项目被放弃,罗姆尼本人被迫辞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一职,从那以后,利用郊区现有的大量资源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努力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十年前,在次贷热潮期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把非裔美国人作为推销次贷的目标。这些贷款的利率爆炸式增长,提前还款的罚款也令人望而却步,导致了一波止赎潮,迫使黑人房主回到贫民区公寓,摧毁了这些家庭搬到的中产阶级社区。巴尔的摩市起诉富国银行,提供证据表明,该银行成立了一个专门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特别部门,受命前往黑人教堂推销次级贷款.该银行没有通过白人机构推销此类贷款的类似做法。这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很普遍,但负责监督借贷行为的联邦银行审查员并没有试图进行干预。当克利夫兰提起类似诉讼时,一位联邦法官指出,由于抵押贷款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严格监管,“毫无疑问,发生在克利夫兰的次级贷款是‘法律制裁’的行为。”
巴尔的摩这一点也不独特美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公共政策,有意地将黑人隔离和贫困化。这些政策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在巴尔的摩看到的骚乱。无论是在1967年引发肯纳委员会报告的骚乱浪潮之后,在1992年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警察被判无罪后引发的洛杉矶骚乱之后,还是在最近警察杀害黑人男子后引发的对抗和破坏行为浪潮之后,社区领袖通常都会恰当地说,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恢复和平之后,我们可以解决根本问题。我们从来不这样做。
当然,巴尔的摩的非裔美国公民是被侵略性、敌意甚至是凶残的警察激怒的,但斯皮罗·阿格纽是对的。没有郊区融合——这在今天的公共政策议程上几乎没有提过——贫民区的状况将会持续下去,导致激进的治安和不可避免的骚乱。就像之前的弗格森一样,巴尔的摩不会是美国不必要经历的最后一场这样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