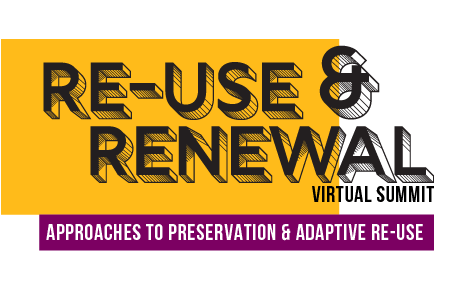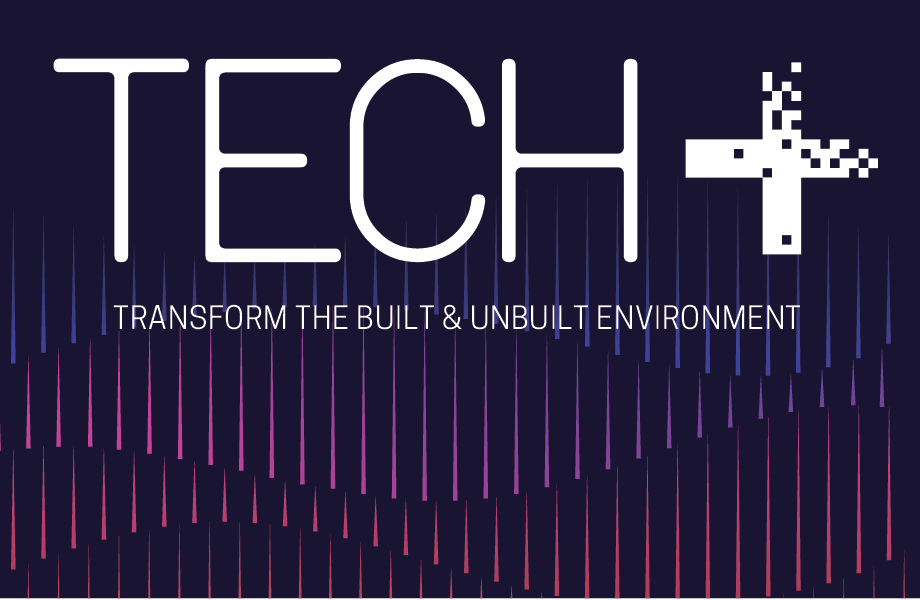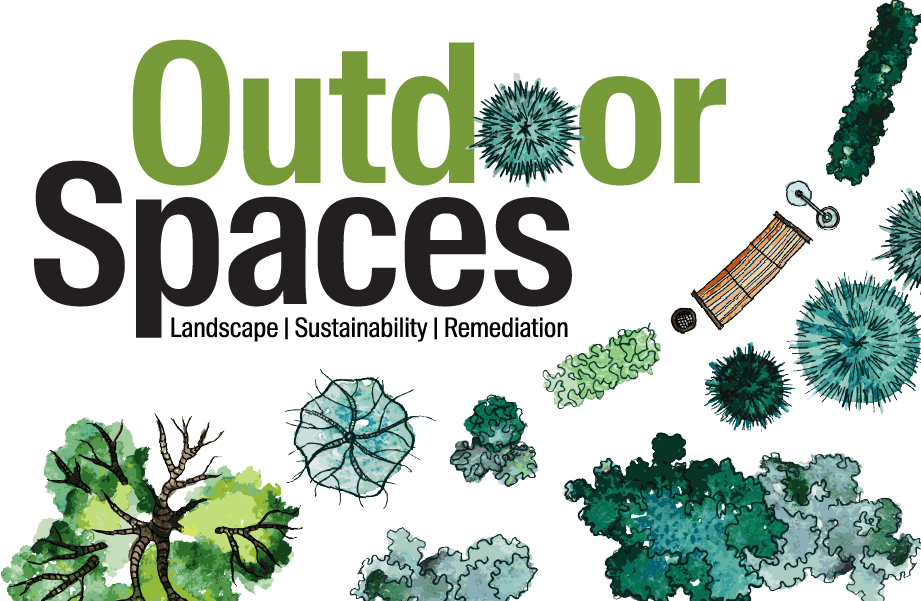公认的建筑历史以断裂为标志,当建筑从根本上改变以响应或服务于新文化范式时,例如古典高雅风格,或对这些风格的风格主义操纵。第一类是先锋派的整个历史,他们的社会和审美目标,以及他们的形式创新。在上个世纪,高度现代主义的精练清晰——本世纪的高级风格——让位于一种缺乏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并倾向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古怪形式。然而,历史往往忽略了那些存在分歧的时刻既不一种可识别的前卫,而不是一种统治的高级风格,伴随着它的矫饰主义的重新投降。
这种线性的历史演化模型可能会被其他时间模型所质疑。根据萨义德(Edward Said)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观察,一个这样的时间模型可能被描述为“迟到”。虽然赛德和阿多诺将迟到作为一种“风格”,但它也可能开始构建一种对那些在统治艺术范式中存在的时间干扰的理解。因此,迟到是一种批判意识,它允许人们选择和消除某些策略。例如,用late是不可能的本身作为一种设计策略。它是一种意识,允许一个人选择一种策略而不是另一种策略。
似乎有两种方式来思考迟到:第一,作为一个时间的时刻,在晚期作品中,不可能毫无疑问地将任何现在,任何时代的精神转化为艺术形式;其次,正如赛义德和阿多诺所说,晚期风格描述的是那些年老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通常是在一生的大师作品之后,拒绝早期作品和宫廷的正式清晰度,而是不和谐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不像年轻的艺术天才的早期作品,他是作为仆人和信使出现的时代精神这位已故艺术家的作品显得不合时宜。在这两种意义上,晚期作品都抵制了对壮观形式和连贯意义的要求。
这种对任何当下时刻的抗拒,或者时代精神,包含了艺术家个人作品之外的含义。晚期(与“晚期风格”相反)不仅暗示了这种时间抵抗模式更广泛的纪律维度,而不仅仅是与已故艺术家的作品相反,而且,剥离了“风格”作为离散美学程序的内涵,假设了一个内部结构维度。因此,迟发不仅仅是一种风格,在任何艺术范式中,迟发都暗示着一种深层时间脱节的潜在存在。虽然“晚期作品”遵循其自身的时间轨迹,可能出现在任何给定的历史时刻(在统治的艺术范式中记录潜在的脱节),但正是在那些主导范式开始失去其结构可持续性的时刻,晚期才不是作为一种异常的艺术风格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记录范式中未言明矛盾的能力。
这并不是一种背离主流范式的转变,而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对这种范式的忠诚,尽管它存在所有的矛盾。伴随着形式上的创造力的明显枯竭,一部晚期作品抵制了追求新奇的动力,而是坚持继续定义纪律的规则和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迟到延长了一个项目的艺术自主权,然而,由于它将一个想法扩展到其极限的动力,迟到发现了一个项目的根本不足,可以说是批评中的批评。
自主性项目对于理解迟到作为一种可能的内部纪律现象是至关重要的。赛义德描述了“忍受以迟到的形式结束但是”的能力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准备或抹杀其他东西。”[1]晚期作品的这种自主模式,它的存在主要是“为自己”,决定了它的流离失所的时间性,它的存在超出了时间。自主的艺术作品遵循自己内在的一套规则,在明显地脱离历史时间的情况下开创了一个内在的时间。迟到挫败了时代精神。
在今天,当学科关注真正崩溃为市场关注和大众媒体的政治影响威胁到建筑或艺术批评的特殊性时,迟滞所固有的批判可能性尤其相关。事实上,在时间上(现在)的滞后与大众传媒影响力的上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筑学科本身好像有点迟到了。对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建筑师来说,自治项目是批判性建筑的试金石,他们会发现一个成熟的解构程序,这种批评的不稳定影响也激发了远不那么清醒的探索,启动了建筑对分裂、蛇形、变形和参数表现主义的兴趣。晚期资本和建筑表达体系的扩张和明显融合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
建筑已经让位于设计。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被视为一种盈余投入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成本。另一方面,建筑是一种多余的存在于任何生产体系之外。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别。作为一种盈余,设计传播着对缺乏批判性内容的新颖形式的无尽的、广泛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不加批判的迟发性(晚期资本的迟发性)与这些伪建筑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用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的话来说,如今占统治地位的建筑类型是“超级鸭子”。也就是说,品牌已经克服了一对一的易读性。这导致了一种媒体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作品的营销变得比作品本身更重要。这产生了建筑表征功能的改变,也是对企业身份结构变化的回应。正如亚历杭德罗·扎拉-波罗在《信封的政治》一书中所说,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日志“现代城市是为跨国股东的利益而建立的,由董事会管理的公司;它是由为跨国利益服务的建筑公司建造的,这些公司购买并经常运营这些建筑....一个人如何构造无面者的脸呢?”[2]当代建筑似乎已经满足了这些对易变的标志性的新需求。“非分层”立面设计的新方法,如参数化过程,只会使建筑几何发展的潜在潜力变得明显,从而产生无限可变的形式。如何选择呢?什么是有效的价值体系?
这种对正式项目的明显扩展,它对产品设计程序的同化,也扩展了内部的操作领域,现在,设计。随着消费者易读性的媒体政治成为构建和感知建筑环境的主导模式,今天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不设计。一个事物的命名,它的感知性和审美性,符合它的交换价值。其结果是:审美创新的驱动力,作为一个封闭的形式主义的一个方面,假定与人类生产的所有领域有更大的相关性。
封闭的形式主义和迟发性——为了创新而创新,而不是对同样的形式主义进行批判——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设计的扩展对构成非设计的部分起到封闭的作用。这一过程既补充又平行于一个日益自治和无处不在的资本体系的运作。晚期资本主义描述了交换关系对政治、社会和审美的兼并。这些资本关系的扩散和强化构成了一个不断扩大和自动生成的运作领域:市场的自主性。
现代主义者对建筑学科自主性的渴望预示着今天市场的自主性。虽然每一种自治都以否定他律为前提,但晚期资本作为一种扩张和整合的计划,将这种差异纳入其自给自足的范围内。如果差异的内在化是任何自治项目的起源,那么建筑,就像其他自治项目一样,已经将市场对新颖性的需求与正式生成和实验的自治实践结合起来。当然,建筑的自主性和市场的自主性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其中一个不排除任何关系,甚至重叠,另一个。相反,自治所依赖的“外部”已经被摧毁了:建筑师Hans Hollein在1968年宣称:“Alles ist Architektur”[3]——处于资本主义晚期和总化阶段的边缘。70年代倡导建筑自主性的人认为恰恰相反,建筑的自主性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可以与其他艺术模式明显区分开来。在最近的衰退面前,这两方面都显得软弱无力。
如果自治有两种形式,那么迟到也就有两种形式。首先,有一个广泛的自治,市场和设计的自治,其次,一个内部组织的自治,语言和一个四面派的“架构”的自治。前者与他物(以外在性或不纯性)融合并包容,而后者则发现这种差异在它很有独创性。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曾提出:“一种自治形式总是同时也是一种他律形式。”这种自主性和他律的巧合在当代审美秩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的美学及其不满朗西埃写道:“因为美学的自主性是一种艺术,在这种艺术中,没有边界将致力于高雅艺术的画家的姿态与致力于娱乐大众的杂技演员的表演分开,没有边界将创造纯粹音乐语言的音乐家与致力于使福特装配线合理化的工程师分开。”[4]
今天的建筑与现代主义遗产的关系暗示了现代主义的两种学科自治版本,既包括扩张的,也包括内部导向的,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他律。当前意义上的建筑不合时宜与其说是反映了时代、风格、艺术作品与神或国家权力的关系的变化——甚至,在简化的意义上,建筑与资本的关系的变化——倒不如说是建筑内部机制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影响,这种不一致被认为是由一种迟到的模式所暴露出来的。
现代主义计划中经验时间的废除(计划作为空间的瞬时阅读)支撑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自主性。当代建筑中平面的退化——平面不再是激进发明的场所——与现代主义建筑时间性的破坏相对应。虽然建筑表面的优势代表了当代建筑的主导模式(并符合景观的时间),但后期的作品继续展现了现代主义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