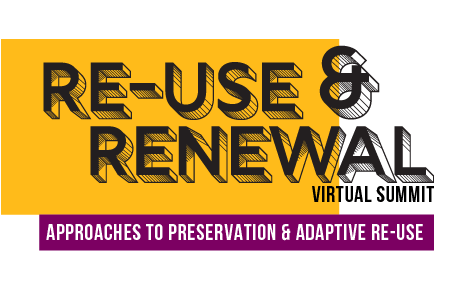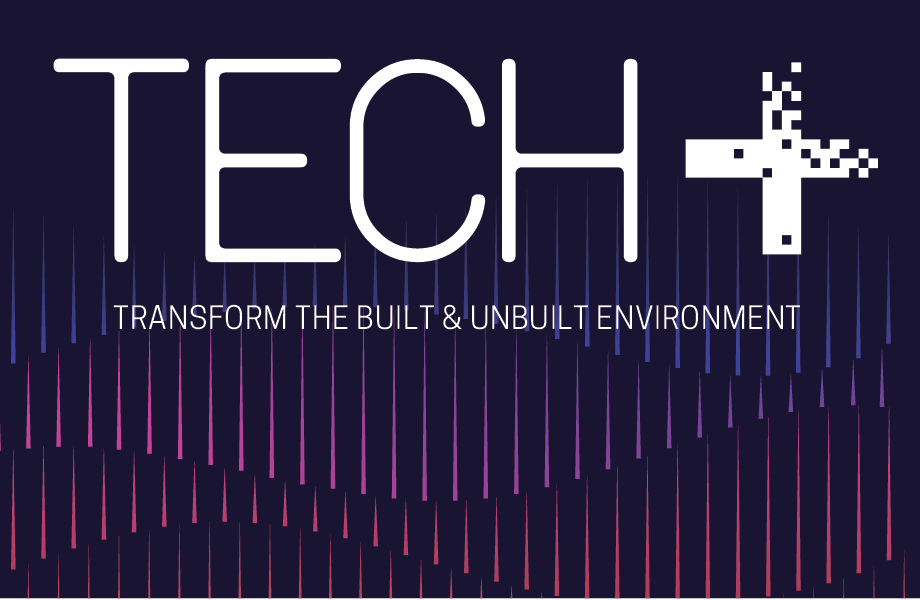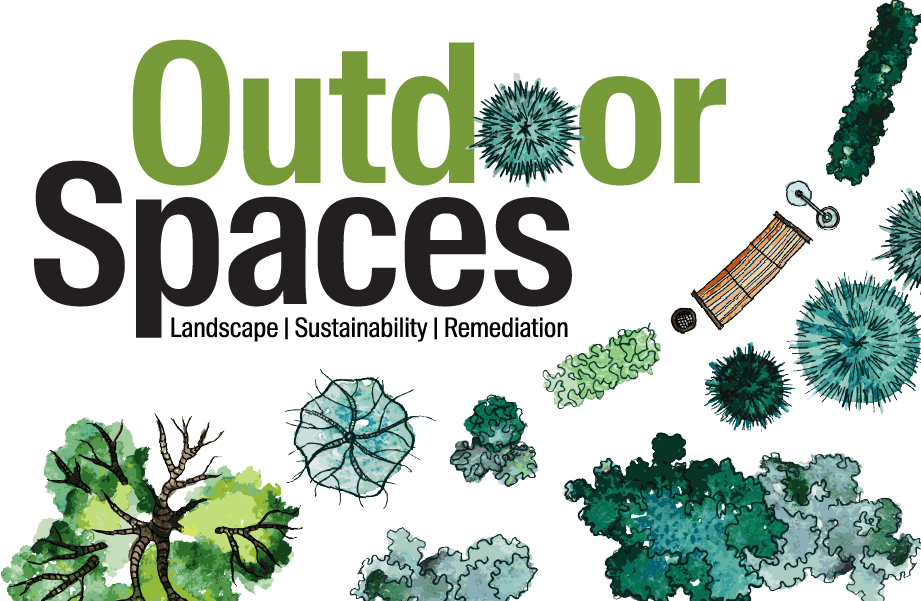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谁需要另一个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雕塑倒在草坪上?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馆长马克斯·安德森问道。“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空间,一种艺术体验,一种永远在变化的景观。博物馆新建的100英亩(100 Acres)艺术公园就有这么大的面积,它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景:在这里,艺术出现在景观之外,或者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创造出的空间和可居住的物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延续几个季节。
这个新展览的地点——一个景观、艺术和建筑的混合体,在世界各地日益流行——是一个位于白河拐弯处和一条拖带运河之间的前砾石坑,这条运河将新公园与奥姆斯特德&奥姆斯特德博物馆场地上的奥姆斯特德景观分开,后者拥有更传统的“plunk艺术”。在几十年前这个坑被捐赠给博物馆后,它仍然是一片荒野,它的空隙被剥去了印第安纳石灰石,充满了水,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游泳洞。
一旦博物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恢复该地区,它就聘请了景观设计师爱德华·l·布莱克(Edward L. Blake),他是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景观工作室的负责人。Blake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教训,告诉我们(景观)建筑可以做什么,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做什么:这是一种休养生养和微妙的调整,其中他移除了大部分非本地的“风”,种植树木和灌木丛来定义更大或更小的空间,蜿蜒的小径穿过公园,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空间出现,序列演变,可以保留的被保留,新的作为对旧的评论或对比出现。
阿肯色州建筑师马龙·布莱克威尔(Marlon Blackwell)设计的一个小型游客中心,与其说是一个焦点,不如说是树林里的一个休憩处,在一个三角形的体块中提供地热产生的温暖或冷却,该体块位于一片Ipe木片夹心的漫滩之上。它是唯一一个或多或少具有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另一个可居住的封闭空间是由艺术家Andrea Zittel设计的漂浮在湖中央的玻璃纤维体块。在夏季的几个月里,艺术学生们住在这里,通过划艇可以到达,它的斑点状形状似乎是当前计算机辅助造型理论的浓缩,但对艺术家来说,它是一个简单的、没有参考意义的形式。
在齐特尔的作品附近,一艘生锈的船似乎正在穿过湖面。它是由Tea Makipaa设计的伊甸园II的一部分,包括岸边的一个警戒塔。在这一点布景设计中,你在塔中听到的隐形演员担心非法移民试图上岸,树林里某处响起了枪声。你可以坐在起伏的长凳上观看这一切,这是肯德尔·巴斯特(Kendall Buster)的作品,它沿着海岸线,为当地渔民提供了一个消磨一天的地方。另一组由Jeppe Hein设计的长椅突然出现在公园各处。它们是一条连续的缎带的一部分,至少在概念上是贯穿公园的,在中间弯道或转弯处露出水面,给你一个坐下休息的地方。
最完整的空间是一个广场,由通常尖锐的政治艺术家阿尔弗雷多·贾尔(Alfredo Jaar)雕刻而成,名为“哀鸣公园”。一条小路引导你进入一个斜坡入地的隧道,然后你走上台阶,进入一个被松动的石墙包围的凸起平台。这是一个孤立的、空旷的、有界限的空间,在那里他鼓励你去思考所有那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或失去亲人的人。然而,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聚会空间,一个野餐的地方,或一个日光浴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明显的人造空间,某种程度上是一座纪念碑,与周围近乎混乱的景观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哀歌公园并不是公园里最好的地方。更成功的是由自称为Type a的艺术家二人组制作的《Team Building (Align)》。它由悬挂在树之间的两个铝环组成。夏至时,他们在自己定义的一小块空地中央投射出一个完美的圆圈,但在其他时间里,他们描绘出一个更加复杂和暗喻的空间,一个你能找到的困难、变化和难以捉摸的完美时刻,就像阿道夫·洛斯(Adolf Loos)在树林中央的墓碑一样。
然而,最热闹的地方是Los Carpinteros的自由篮。它的蓝色和红色的钢圈环绕着两个篮球篮板,模仿可能的投掷和跳跃。它形成了公园的后门,已经成为邻居孩子们玩耍和玩艺术的热门场所。在这里,“100英亩”实现了其艺术作为社区日常生活真实部分的目标,它来自并提供了一种替代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选择。安德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博物馆可能会增加一些作品,而随着它们的恶化,一些作品可能会消失在景观中。但100英亩仍将是一个景观成为艺术的地方,而且艺术看起来非常像优秀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