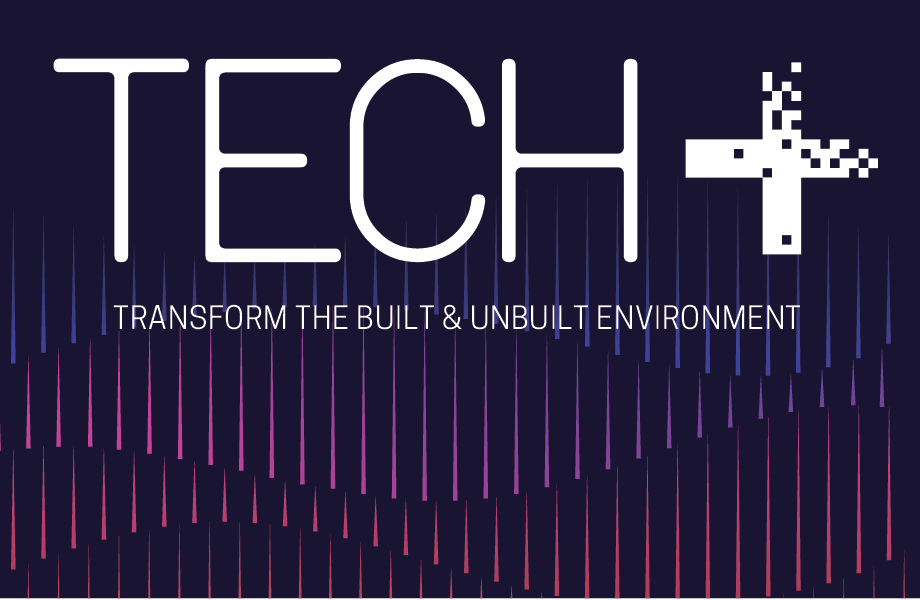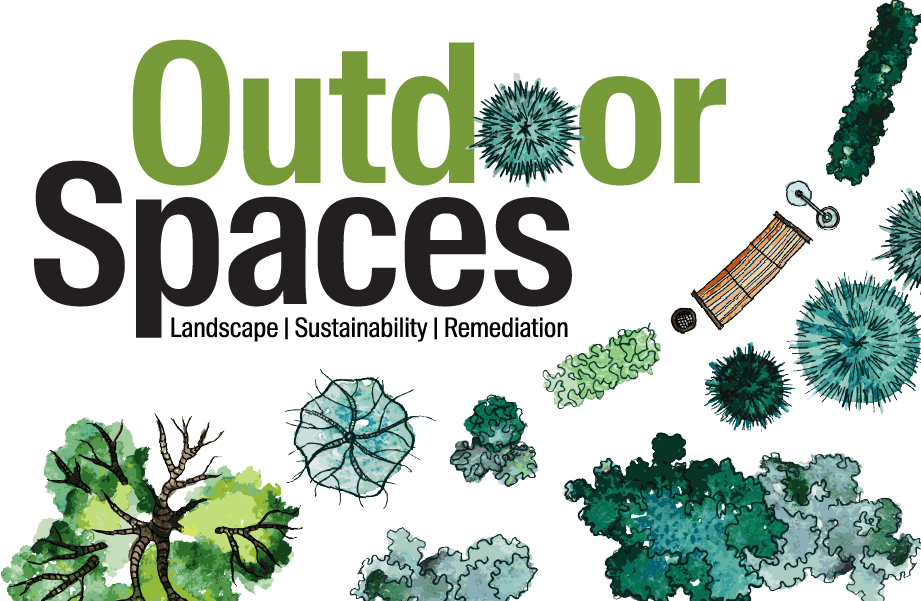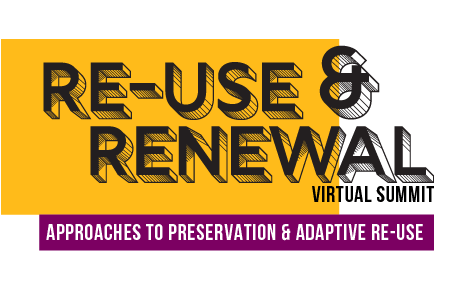2020年5月,面对隐私倡导者越来越多的批评,人行道上的实验室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多克托罗夫宣布这家谷歌支持的公司将取消其在多伦多码头区(Quayside)的智慧城市项目。随着它的消失,批评家们有一种感觉,某种邪恶被打败了——小人物赢了,Alphabet/谷歌被打败了。当人行道正式停止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平行时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项目中,人们的反应同样是欢欣鼓舞的,尽管更为压抑。
在此之后,Sidewalk本身似乎已经销声匿迹,悄悄地为自己的一些定制技术申请了专利。同样,智慧城市梦如今,多伦多滨水区(Sidewalk的前政府合作伙伴)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开发合作伙伴。有希望的候选人将在一场国际竞赛中竞争,迫使提案考虑到“2020年的经历,包括COVID-19大流行、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安全和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
很容易读懂新的码头区比赛标准这是对Sidewalk Labs竞购所宣扬的美德的直接指责。几乎所有关于智能技术的提及都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包容性和弹性的精神。保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对大规模木结构的兴趣,有趣的是,Sidewalk自己的动态店面方案被称为Stoa,已经被压进了“以人为本的愿景”的服务中《卫报》把它。(这家新闻机构在没有任何确定的项目材料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这很能说明问题。)
然而,在庆祝“多伦多人行道”(Sidewalk Toronto)的消亡、被“多伦多滨水区”(Waterfront Toronto)取代的时候,活动人士和记者们都误读了形势。前码头区项目,想象成一个由Snøhetta和Heatherwick工作室设计的木质庭院他从来都不是智慧城市的官方代表,而是一个相对的异类。它的目标不同于美国真正的智慧城市,远没有被击败,而是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直以来,Sidewalk Labs将其项目描述为一个以空间为起点和终点的城市创新,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导。任何给定的智能城市的空间组成部分——码头或其他地方——只是一个巨大的利维坦看得见的眼睛;如果有人设法蒙蔽了它,它就会继续不减地进行它那残酷的工作。
尽管如此,这只野兽还是很无聊。所有那些华而不实的效果图、闪闪发光的流行语和可供展览的原型,都是为了掩盖智慧城市作为标准发展指南的真正功能。作为一个2017年彭博智能城市小组他断言,智慧城市项目的总体目标不是充满技术的建设,而是“利用创新的融资模式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克服财务障碍,帮助实现基础设施改善目标。”这与Sidewalk兜售的英雄愿景相去甚远。考虑到该公司的大部分研究和建议都涉及对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从道路到建筑物)的彻底重新构想;再想想城市仪表盘和响应式环境对潜在居民的承诺。总之,Quayside试图将智慧城市定位为一种提供给奋斗者阶层的华丽生活方式产品。与此同时,在公私合营的城市体制中,智慧城市唤起了许多相互关联的优化或紧缩项目。
也就是说,智慧城市市场真正的权力和金钱不在于Sidewalk Labs相对本地化且容易受到抨击的技术未来,也不在于最近,丰田在日本华丽的编织城不仅如此,在智库、行业出版物、市长联盟、大学项目和后疫情重置会议上也会出现。按照big设计的编织城市(据说去年冬天已经破土动工)的路线,实现一个设备齐全的“试验台”城市主义,与普遍的前景相比,显得苍白无力。例如,将现有城市减少到纯粹的量化,直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与其他任何城市一起评估。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将城市和“城市性”重新定义为一系列可解析的标准、发展目标和智能排名,这些标准、目标和排名最终决定了资金的可用性和潜在投资者的意愿。
伊甸战略研究所其他行业观察人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断言智能城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4.0城市,从而预示着焦点将从技术本身转向人。到目前为止,获得这一称号的20多个城市都在追求无数的智慧城市项目(平均14个!),投资于更好的基础设施,将疫情的见解纳入规划模型,并密切关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居民4.0”渗透在城市4.0的明智和生态友好的交通枢纽,公园,共同工作空间等中,同样是一个拥有“聪明技能”的模范员工,他们利用人才学习机会和适当的国际生活(工作时间允许)。
除了这些智能城市项目(几乎所有项目都在全球北方)之外,智能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长期的部署发展学家行。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政策专家中广受欢迎,但它重演了同样的经典把戏,即在政治经济大棒的末端悬挂发展胡萝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仍在继续扮演它们的经典角色。)然而,从发达/不发达国家到发达/不发达城市的规模缩小,加深了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以哥伦比亚Medellín为例,其出版物如《新闻周刊》和外交政策无数白皮书都将其誉为“创新之城”。外交政策指出地铁缆车是时代的标志,声称Medellín,一个被一个世纪的内战和毒品交易所束缚的地方,现在闪耀着聪明,创新政策的光芒。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所有的当代城市发展都等于“聪明”吗?一个城市财富的改善是否应该自动赋予其市长或市政集团天才的地位,就像Medellín发生的那样?
但不要管那些天才了——智慧城市的英雄时代随着Sidewalk Toronto的死亡而结束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胜利。可以说,智慧城市从来都不是“面向对象”的,而是一种建立在政治本身根据科学发展原则(或技术)行事的理念之上的精神。即使智慧城市原则在各地生根发芽——不仅在多伦多或塔林,而且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它们也只不过是标准的环境改善计划,比如安装交通摄像头或道路施工。智能的魅力卖点——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总是徒劳无功,或者像哥伦布一样,智慧城市项目被抛弃的第一个要素。
然而,聪明已经定义了这个世界:它是治理、政策、紧缩、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新口号。也许最隐蔽的是,它获得了一群自封的进步人士(yimby、生态城市类型、15分钟城市追随者等)的支持,这些人认为资本入侵城市空间是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的唯一途径。所有人都团结在发展的旗帜下,因为首都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后发起了又一次回归城市的运动。我们这些寻求实际的、实质性改变的人——积极分子、激进分子,甚至批评者——必须改变策略,否则我们就会被贴上不可救药的唱反调者的标签。我们的批判首先必须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精明作斗争。
因为没有孤立的智能项目。把它们当作这样或特别反常的行为来讨论是没有用的坏演员们用这个或那个坏技术还是政策。与聪明的世界观作斗争,首先需要发展一种同样全面的世界观,否则我们至多只能在已经输掉战争的情况下赢得某些战斗。
凯文·罗根是一名作家、设计师、学生和业余爱好者,住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