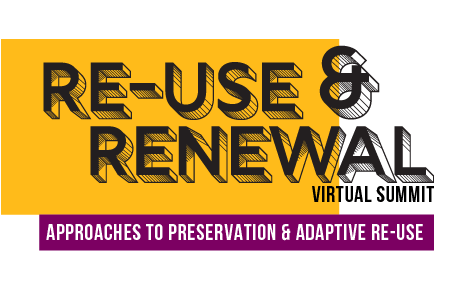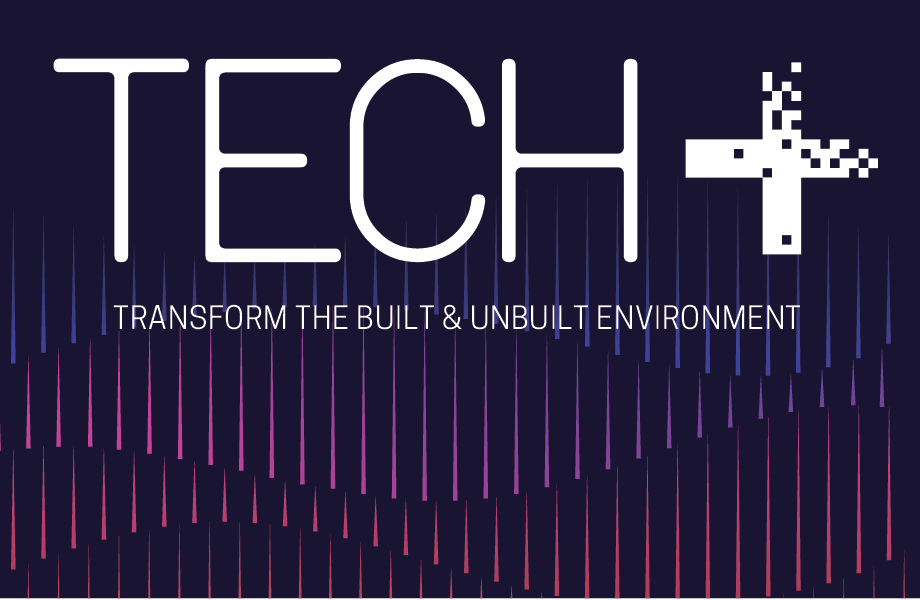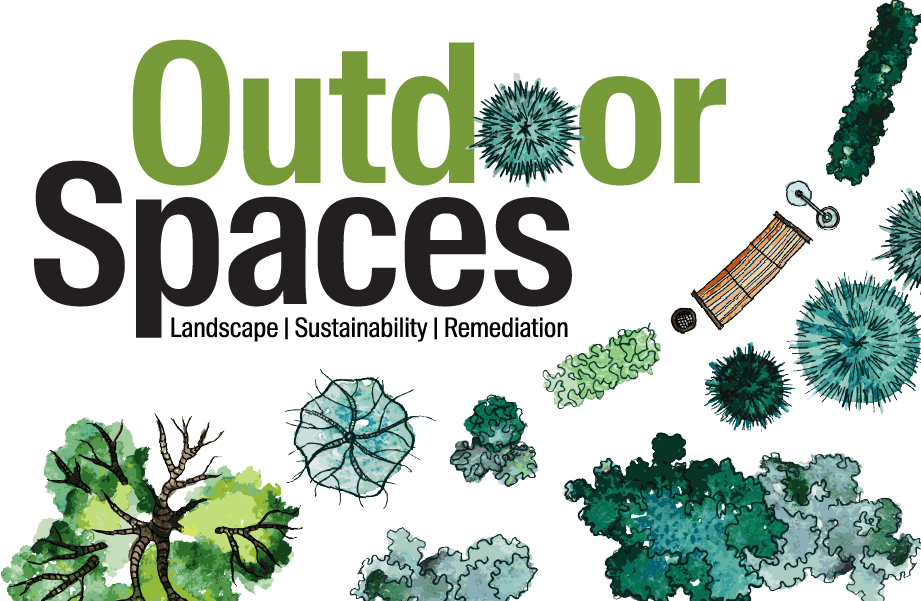在美国,在建筑专业和建筑学术界的残疾人在统计上是不可见的。无论是美国建筑师学会,全国建筑注册委员会美国大学建筑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也没有收集有关美国自认为有身体或认知障碍的建筑师或建筑专业学生数量的数据。纽约城市学院伯纳德和安妮·斯皮策建筑学院j·马克斯·邦德公正城市设计中心发表的开创性报告《建筑中的包容》(Inclusion in The Architecture)不包括残疾方面的数据。
在美国,缺乏对残疾建筑学生和建筑师的了解,与在多样化、公平和包容性方面取得的其他进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建筑师这个职业的自我审视——从数据上和文化上——已经迫使谁能成为美国的建筑师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大学的出勤率、教职人员的任命和专业活动的代表来看,建筑似乎比50年前在种族和性别方面更加多样化。从著名建筑师到最精英建筑学院的院长,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化的努力正在产生影响。

多样化在建筑中至关重要,因为关于种族、性别、能力和残疾的观念在建筑和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建造中形成和再现。在美国,残疾建筑学生、建筑师,特别是学术和机构领袖的缺乏,使残疾人成为讨论的话题,而不是变革的推动者。事实上,残疾理论的一部分认为,残疾是一个相对的范畴,构建在产生残疾身体和精神的空间中。但是,无论是被视为先天的还是相对的,医学敏感性支撑了许多关于建筑中残疾的讨论,因为如果考虑到残疾人,他们是空间中的主体,而不是空间的创造者。这是由于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阻止残疾人想象一个他们参与建筑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未来。
限制建筑作为一种职业的可达性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建筑教育的实际建筑。虽然许多建筑学校完全对残疾人开放,但大多数常春藤名校的建筑-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历史上为下肢残疾人士提供了物理上无法进入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法案通过多年后美国残疾人法案(ADA)、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仍然有轮椅残疾人无法使用或难以使用的设施。几乎所有这些建筑学院都进行了翻修,但关键空间——讲堂(特别是讲堂的讲台,人们在那里演讲)、海报空间、办公室——仍然无法进入或难以进入。同样,许多学校都存在这些问题,但这些精英机构对这一职业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
我们已经失去了几代残疾建筑师领袖,他们可能提供了建筑的关键观点,不仅是因为精英机构的建筑字面上构建的障碍,也因为我们想象建筑知识生产的方式。例如,建筑教育需要对历史先例的全面了解,但我们如何想象获得这些知识的空间呢?想象一下,要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这植根于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罗马广场(Roman Forum)或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等众多遗址。对于身体健全的人来说,这些景点是具有挑战性的地方——这一观察结果被包括勒·柯布西耶,路易斯·卡恩,阿尔瓦·阿尔托.
但是,雅典卫城和罗马广场在几千年前(以当代的标准)都比它们今天作为“现代化”的建筑保存场所要容易得多。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观念,在体力消耗下体验废墟,已经永久地融入了许多重要的建筑纪念碑的体验中。这是史学美学的一个关键方面,在建筑历史实践的文献或教学中几乎没有探索过。换句话说,身体与历史空间关系的浪漫主义笼罩在建筑史的经验之上,这在教室中这些偏远地点的描述和我们对过去经验的期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说教育和历史知识空间的设计塑造了建筑师能力的想法,那么在建筑实习中遇到的物理空间也需要批判性的分析。《美国残疾人法》使美国的身体和认知残疾人士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所有类型的建筑和公共空间。然而,ADA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建筑工地。即使美国的建筑学院共同努力改善无障碍环境,但仍有一些障碍阻碍着各种残疾的学生成为建筑师。如果不能在办公室的建筑表现形式的制作和建筑现场的材料组装之间的关系中导航,几乎不可能进行建筑实习。
想象建筑工地的可达性增加是乌托邦式的,但却是必要的,主要是因为这样做将重新想象那些创造出适合的建筑的人的类型。工会可能会采取这一措施以促进工作场所的安全。在这个极其危险的行业中,后者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在45年的职业生涯中,从事建筑工作的人有75%的几率因工伤而致残。建筑工作只占美国就业的3%,几乎占所有工伤事故的四分之一。因此,我们到达了关于残疾和建筑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建筑的建造比任何其他经济部门产生的残疾更多。
想象建筑的可达性,从挖地基的人延伸到使用室内的人,使我们能够在本体层面上重新想象建筑是什么。它从根本上将残疾人从空间的主体转变为建筑概念化和建造的主体。

建筑师和建筑专业学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关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论述在建筑学术界和更大的专业领域产生了可衡量的变化的时代。这导致了新一代的非裔美国人,Latinx全球建筑史课程的扩大,以及关注种族和性别的学生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成果。是时候让残疾人参与到美国建筑教育和建筑行业发生的重要转变中来了。当然,这些形式的识别并不是孤立的,有机会理解各种形式的主体性和残疾之间交叉和相互加强的关系。
近年来,学术建筑小组、期刊和研讨会将残疾视角引入建筑。这些都是重要的贡献。然而,在许多场馆中,没有永久性和严重残疾的建筑师在场,以代表这种特殊形式的身份。正如本文所展示的,作为一名残疾架构师,其职业结构的限制是根深蒂固的,而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能力的限制也是根深蒂固的。
想象残障人士在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仅是让建筑更容易进入,或者识别残障人士,并邀请他们进入这个行业。这将涉及对学院和大学的物理空间进行昂贵的改造;建筑历史、理论和设计中运动美学的弱化;法律结构将向更多的人开放建筑业这样的领域。
如果我们在空间、话语和建筑的可达性方面追求这些转变,我们可能会看到想象成为建筑师并领导这一职业的人的类型发生平行转变。相应地,对可达性及其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的实现的讨论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复杂的和道德的发展阶段。
大卫·吉森(David Gissen)是加州艺术学院的建筑学教授。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还是一名建筑系学生的时候,他就做了膝盖以上截肢手术——这是一项与童年早期疾病有关的手术。